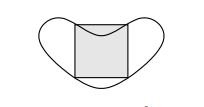解决最难、最简单问题的数论家
当詹姆斯·梅纳德(James Maynard)三岁时,一位健康访客来到他位于伦敦东北部切姆斯福德(Chermsford)的家中,检查他的发展情况。这样的探视对幼儿来说是例行公事,评估员带领他通过了一系列标准的测试。只有一个问题:梅纳德认为他们很愚蠢。
因此,当她给他一个形状排序任务时,他故意将形状按令人惊讶的顺序排列,然后详细解释为什么他的解决方案比她的更有趣。当她问他玩具农场里的牛是什么动物时,他的母亲吉尔·梅纳德(Gill Maynard)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他真的很喜欢告诉她这是‘绵羊’,并观察她的反应。”当他认为评估已经进行了足够长的时间后,他宣布评估已经结束,并拿出了他的乐高积木。
吉尔·梅纳德(Gill Maynard)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一个三岁的孩子摧毁了这个可怜的女人。”
评估员告诉他母亲詹姆斯缺乏纪律。“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他在学校会有真正的问题,”她说。
类似的事件在梅纳德的学校生活中屡见不鲜。有一次,他的物理老师使用了一种评分标准,梅纳德认为这很荒谬:没有解释或单位的正确答案只得三分之一的分。为了表示抗议,梅纳德只写了答案,全部答对,得分33%。“我想老师可能已经受够我了,”他说。
“我绝对是那些烦人的孩子中的一员,他们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直都是,“梅纳德说。在他的学生时代,他“想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至少想要为事情找理由。”
因此,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在2013年,作为一名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26岁的梅纳德在博士后导师警告他不要回答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时,只是耸耸肩,这个问题是关于质数(那些只能被1及其本身整除的整数)的最核心问题之一。
梅纳德当时在蒙特利尔大学的导师安德鲁·格兰维尔(Andrew Granville)回忆道:“我有点像是对他说,‘我希望你不要全职工作,因为我真的很有信心,你会失败的。’”
但梅纳德“仍然有勇气,”蒙特利尔大学的迪米特里斯·库库洛普洛斯(Dimitris Koukoulopoulos)说,“他只是坐下来说,‘好吧,让我试试这个想法,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牛津大学的本·格林(Ben Green)说,他需要的是一个定理,这个定理“促使数学家们对质数之间的间距进行了重大的重新评估”。梅纳德现在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教授。
梅纳德被有关质数的问题所吸引,这些问题简单到可以向高中生解释,但又很难,足以让数学家们难倒几个世纪。他说:“简单和基本之间的对比,(和)仍然完全神秘之间的对比,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这样的问题很多,但现在比梅纳德出现之前要少。因为他早期的成功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关于质数和相关结构的一系列发现中的第一个。现在他的博士学位已经过去七年了,梅纳德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上领先的数字理论家之一。
格林说,他在成为一名世界上受人尊敬的数学家的过程中经历了“非常陡峭的上升轨迹”。
格兰维尔正在写一本关于解析数论的书,他抱怨梅纳德大大放慢了他的进步。“因为他,我不得不多加150页,”格兰维尔说。
今年1月,在丹佛举行的联合数学会议上,我与梅纳德坐在一起,他前来领取弗兰克·纳尔逊·科尔数论奖(Frank Nelson Cole Award In Number They)。虽然这一奖项正式授予一篇著名的论文,但在梅纳德的案例中,奖项委员会忍不住引用了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都出现在顶级数学期刊上。
他只为他的丹佛之行安排了一天半的时间,但尽管我们在他从英国抵达后仅仅一个小时就见过面,他的脚步还是充满了活力。“我还在兴奋呢,”他笑着说,他那张狭长的孩子气的脸张得更大了。“时差还没有影响到我。”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笑容满面,除了他必须摆姿势拍照的时候。“人们说我不知何故无法在照片中露出合适的笑容,”他做了个咬牙切齿的鬼脸说。
如果时间允许,梅纳德计划在城市里漫步拍照。几年前,他开始摄影是为了感觉自己与他出差的许多城市更有联系,但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痴迷。他说:“我夏天去了香港,黎明时分我要徒步旅行,拿着三脚架拍照。”尽管他通常不是个早起的人。
梅纳德一直都有这种强迫症,小时候他经历了不同的恐龙、地质学和天文学阶段。他说:“我非常不擅长对事物有适度的兴趣。”“不知何故,我必须对它着迷,否则我会完全放弃它。”
他的父亲克里斯·梅纳德(Chris Maynard)说,一旦梅纳德对一个主题产生兴趣,他往往不会停止,直到他的能力达到极限。“但他的数学还没到那个地步。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他的动力所在。“。
尽管梅纳德家的其他人都以人文学科为导向-他的父母是语言教师,他的兄弟学习历史-但他总是发现自己走上了提供最多数学的道路。他说:“考虑到我当时的感受,在每个阶段,我都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下一步。”
在牛津大学研究生院时,他非凡的数学能力变得显而易见。他的导师罗杰·希思-布朗(Roger Heath-Brown)说,到了博士学习的后半段,他们的会面感觉更像是合作,而不是指导。“我以前从来没有和研究生有过这种感觉,”他说。
当梅纳德离开牛津前往蒙特利尔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时,他已经开始考虑一种潜在的方法来理解质数之间的差距。通常,沿着数字线走出去,质数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但在某些方面,它们的行为也像是随机数的集合,所以数学家们预计它们的间距通常会比平均水平近得多或远得多。数学中最著名的问题之一是孪生素数猜想,该猜想假设有无限多对素数只相差2,如11和13。
梅纳德怀疑,使用大约10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描述的过滤质数的方法,可能在理解质数间隙方面取得进展。虽然数学家们已经仔细研究了这种方法,但梅纳德认为应该有可能从这种方法中提取更多的果汁。他说:“我一直在做计算和计算,我不断地得到这些小信号,这表明有一些东西需要理解和发现。”“不知何故,我完全被它迷住了,我真的想继续下去,直到我能想出一种方法来解释我看到的东西。”
他的博士后导师格兰维尔劝阻梅纳德不要走这条路。格兰维尔说:“我真的不完全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有可能奏效。”但是“詹姆斯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怀疑而退缩,事实上,他只是笑了笑。”
在梅纳德早期的探索中,数论世界发生了一次地震事件。一位名为张一堂(音译)的鲜为人知的数学家证明了,这不完全是孪生素数猜想,而是第二好的事情:他证明了有无限多对素数至多相隔有限的距离(准确地说,是7000万对)。这一发现为张赢得了立竿见影的荣誉,形式包括多份工作邀请(包括一份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的工作,他现在在那里任教),邀请讲座,新闻故事,甚至是一部纪录片。
与此同时,梅纳德继续致力于自己的方法来理解素数差距,大约六个月后,在灵光一现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一种完全独立的、比张的方法更强大的方法-它建立了无限多对素数最多相差600个。梅纳德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素数对,还适用于三倍数、四倍数和更大的集合(每个集合有不同的界限)。斯坦福大学的Kannan Soundararajan说:“这个结果看起来令人惊讶,太好了,简直不像是真的。”
事实上,当梅纳德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兴奋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波恐惧,认为他错过了一些明显的错误。幸运的是,他说,“当我突然害怕我的结果是错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更高了。…。没有什么比恐惧更能激励我了。“。
格兰维尔坚持让梅纳德在写下他的结果时把每一个细节都写清楚。“没人会相信你,因为没人听说过你,”他告诉梅纳德。“你必须把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没有人能和你争辩。”
在这个过程接近尾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可能很容易让一位年轻数学家感到恐惧的事情:梅纳德和格兰维尔私下了解到,另一位数学家在相同的时间框架内得出了基本上相同的结果。而且不是普通的数学家,而是现代最多产和最受尊敬的数学家之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菲尔兹奖牌获得者特伦斯·陶。这个问题引起了陶渊明的注意,当时他和其他数学家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合作,以减少张的证明中7000万的界限。
当陶渊明得知一位鲜为人知的26岁的年轻人证明了同样的事情时,他一直对自己的新结果感到相当自豪。“老实说,从他写出来的方式来看,他的结果实际上比我要干净,”陶说。“他证明了略微更有力的说法。”陶渊明大方地避免宣布自己的工作,以避免让这样一位年轻数学家的成就黯然失色,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和梅纳德联合撰写一篇论文,许多数学家会认为陶渊明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创造性工作。
很容易想象另一个时间表,在这个时间线上,张在梅纳德之后6个月而不是之前6个月证明了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的探索可能会被推迟,或者干脆被阻止)。那么所有的荣誉都将属于梅纳德,而不是张。但梅纳德对事情的发展并不感到羡慕。“当张证明他的结果时,我非常兴奋,”他说。“我得到的主要快乐是从解决问题中获得的。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太多,‘哦,要是我做这件事稍微不一样就好了。’“。
梅纳德经常选择不戴眼镜从家里漫步到办公室。这种温和的模糊有助于他专注于数学,但有时也会导致他从他的伴侣埃莉诺·格兰特(Eleanor Grant)身边走过,而没有认出她。牛津的一名医生格兰特说:“有一次,他认为他看到了我,他真的非常非常自豪地看到了我,然后跑到这个长得一点也不像我的人跟前。”
梅纳德在这一点和其他几个方面都符合心不在焉的教授的刻板印象。例如,他几乎总是穿着相同风格的衣服,一件开领的白色衬衫和牛仔裤。“我显然不是最注重时尚的人,”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有一次,作为一个恶作剧,所有参加他的一次演讲的数学家都穿着梅纳德的制服出现了。)。
但他也掩盖了许多关于内向数学家的陈词滥调。同事们称他热情、爱开玩笑、性格外向。在大流行之前,他每天午饭后都会带着自己的咖啡豆去上班,并为其他数字理论家煮咖啡。希思-布朗说,几年前,当他在伯克利的数学科学研究所度过一个学期时,他与另外两名年轻数学家共同居住的房子是“派对屋”(尽管梅纳德将其称为“以数学家的标准衡量的派对屋”)。
格兰维尔说,由于梅纳德的存在,许多新一代的数字理论家更具社会性。“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团队的中心。”
在梅纳德证明了他关于素数之间小间隙的定理后,数学家们急忙将他的见解应用到其他问题上。但到目前为止,这样做的最大成功来自梅纳德本人,他想出了如何解决巨大的质数差距,比之前75多年来没有看到重大进展的估计有所改善。格兰维尔说,梅纳德将他的方法适应于这种新的情景“是我在数论中见过的最聪明的把戏之一”。
Soundarajan在谈到梅纳德关于素数差距大小的结果时说:“我想说,任何人都会很高兴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证明了两个这样的定理。”“他是在刚读完研究生之后才做这件事的,这一点是相当了不起的。”
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小缺口故事的呼应中,陶渊明再次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尽管这一次他与格林和另外两名合著者合作)。从那时起,梅纳德和陶渊明得出类似结果的倾向就成了数论界的笑柄。一两年后,当陶渊明解决了另一个长期存在的数论问题时,他说:“我记得当时非常偏执,只是问安德鲁(格兰维尔),‘我真的希望詹姆斯这次没有再抢我的便宜。’”
从那时起,梅纳德向数论界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仅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的克隆。例如,去年,他和库库洛普洛斯解决了一个有近80年历史的问题,名为达芬-谢弗猜想(Duffin-Schaeffer Conjection),该猜想询问哪些无限的分母集合产生的分数在逼近无理数方面做得很好。“这只是…某一地区的圣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近似值,“Granville说。
几年前,梅纳德解决了可能是关于质数的终极问题,这个问题很容易陈述,但很难证明,他证明了无限多的素数没有任何7(或者你可以选择的任何其他数字)。虽然如果你看的是小数字,不带7的数字是很多的,但是当你开始看,比如说,1000位数字时,它们几乎是稀有的,所以要想证明这个稀疏的数字集合包含无限多的质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希思-布朗说:“这是人们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疑惑的事情,但还没有人接近于证明这一点。”
这个问题在10个以外的其他基地都是有意义的,梅纳德首先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基地的证据。基数越大,证明这类定理就越容易,因为如果你所在的基数有一百万个不同的数字,而不是只有0到9,那么像“没有7”这样的限制就会产生较小的影响。格兰维尔说,梅纳德对大型基地的证明“非常优雅”。
但是梅纳德开始痴迷于用普通的10进制证明他的定理。“从数学角度看,以10为基数有点武断,但…。这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谈论的基地,“他说。
从100万的基数开始,他不断减少基数,先是减到5000,然后是1000,然后是100。“这几乎成了我自己的一场游戏,关于我能想出一个多么复杂的论点,”他说。“这几乎就像这些投注机或这些在线游戏,每次都会给你一点内啡肽的打击。”
他在12垒被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让他担心最终的目标会逃脱。但最终他到了10垒。他说:“我非常高兴能拖着自己冲过终点线,然后宣布胜利。”
梅纳德必须发明各种各样的新点子才能到达10垒。“这显示了他作为一名数学家的绝对、非凡、强大的力量,”格兰维尔说。
这一贡献和其他贡献在数字理论家中引起了能量和期待的嗡嗡声。希思-布朗说:“我不确定目前解析数理论中还有谁能产生更多的兴奋。”
“人们在想,‘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他说。“一切似乎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