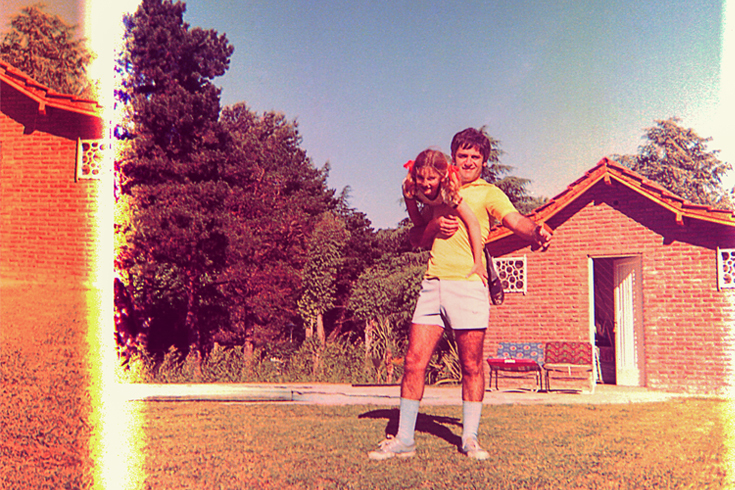为什么怀旧是我们的新常态
在一种完全不可调和的气氛中。当然,有一种感觉,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从根本上不可能的渴望,一种想要回到过去的渴望,即使我们被不断地驱赶着前进,即使我们坐在那里沉思,也被推得离我们的愿望越来越远。但它也是真实的感觉,不断地抵制任何给它形状或感觉的尝试。如果我们说我们怀旧,总体上或对某件事特别怀旧,这很少需要解释,而且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好的解释:为什么让我们倒退的是祖母饼干的味道,或者特定毛衣的手感,或者是看到某个操场上的某棵树,而不是其他什么?为什么在一个原本平淡无奇的周二,它会在现在涌出呢?为什么我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这有什么关系?这假设我们甚至想过要审问这种突如其来的匆忙:怀旧的一个更持久的品质是它能够逃避理性,在不引发任何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被深深地感受到。
正是这种难以捉摸的神秘光环让怀旧看起来不像是某种现代状况,而更像是一种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清楚的普遍感觉。如果感觉通常是需要表达的内在体验,不管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么我们无法真正做任何怀旧的事情,可能是我们让它保持了这么长时间无法言说的原因。大多数类型的渴望都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解决,如果不一定能让渴望者满意的话。怀旧只能活着或者放弃:它是一种被提炼成本质的向往,向往不是真正为了它自己,而是因为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也许它抵制定义太久了,因为命名它无论如何都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
对于这个概念的难以捉摸,怀旧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并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那样-同样恰当的是,它是伴随着对没有词来描述它的那个时代的渴望而创造出来的。1688年,一位名叫约翰尼斯·霍弗(Johannes Hofer)的瑞士医科学生给一种他在被派往国外的瑞士年轻人身上注意到的疾病起了“怀旧”的名字。这些年轻人主要是雇佣兵,这是瑞士当时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但也有家仆和其他发现自己在“外国地区”的人。就像当时“比流血的体液更复杂的医学”这一新兴领域的风格一样,霍费尔使用了古希腊语含糊不清的夸张形式的合成词:nostos大致表示“家”-尽管它更多地表示“回家”,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希腊文学的一个子类别的名字,最著名的是“奥德赛”-而algos的意思更简单,指的是“痛苦”,源于algea,悲伤和悲伤的人格化,以及。(如果你想要激起老板的过度同情,比如,告诉他们你有头疼或肌肉痛--分别是头痛或肌肉酸痛。)。
因此,怀旧的字面意思是“与家相关的痛苦”--或者,用稍微熟悉的术语来说,就是“想家”。这不是巧合,但更相关的是,这也不是花哨的医学用语被愚弄以供大众消费的情况。至少不是笼统地说:英语单词“乡愁”或多或少是乡愁的直接翻译。但最初的术语是法语,maladie du Payer,它不仅特指瑞士人强烈怀念祖国的倾向,而且比霍费尔至少早了30年。霍费尔的发明带来了特定的医学层面,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他那个时代存在的医学一样:霍费尔的观察相当详细,但仍然完全是轶事,并受到许多猜测的影响。他用语言学弥补了他在科学严谨性方面的不足,试图用多个名词来证明医学对这个概念的统治是合法的,包括厌食症(对家的痴迷,你很快就会看到,这可能更准确地描述了他构思的“疾病”),爱房症(痴迷于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多年后在他的论文第二版中,pothopatridalgia(由于对父亲家的渴望而产生的痛苦,
虽然纯粹的乡愁和医学怀旧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古代语言的例子,但霍弗仍然描述了一种严重的疾病,这种疾病可能会从简单的身体疾病,如耳鸣或消化不良,发展到接近紧张症甚至死亡。根据霍费尔的说法,它的根本原因是“动物精神通过中脑的那些纤维持续不断地振动,在这些纤维中,留下了祖国思想的印记。”正如赫尔穆特·伊尔布鲁克在他的书“怀旧:起源与终结”中所解释的那样
到了19世纪,怀旧的恐惧终于蔓延到了其他国家的士兵身上。为了阻止疾病的传播,俄罗斯医生建议活埋任何开始出现症状的人-这显然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年轻的战士们爆发了几次疫情,尽管从技术上讲,他们本身从未离开过自己的祖国。他们的医生稍微仁慈一些,建议偶尔离开前线战斗会提振他们的士气(这并不是说医生们没有怀疑怀旧情绪也暴露了士兵性格中的一个深层次缺陷)。美国军队显然一直在偷偷探索这个概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为了减少开小差。在20世纪上半叶,怀旧保持了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一些兴趣,尽管形式有所降低:它变成了与其说是疾病,不如说是症状甚至性格,通常是那些有更大、更紧迫问题的人的怀旧情绪。在20世纪上半叶,怀旧仍然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兴趣所在,尽管形式有所下降:它变成了与其说是疾病,不如说是症状或性格,通常是那些有更大、更紧迫问题的人。(1987年对其常见的历史-心理引用的一项调查引用了“对与恋母前期母亲结合的强烈渴望,对童年的悲伤告别,对哀悼的防御,或者对永远失去的过去的渴望”。)。然而,尽管有这些最后的触须,内战确实是最后一次有人被诊断为怀旧者,因此: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怀旧在很大程度上被医学界抛弃了。这似乎与其说与大脑结构或心理健康方面的任何特定突破有关,不如说与任何人在理解怀旧方面普遍无法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有关,更不用说治愈怀旧了。
然而,当它走出医学领域,进入文化领域时,怀旧并没有完全摆脱它奇怪的污名。它首先在哲学和理论界站稳脚跟,尽管它与乡愁的概念可以互换使用,在那里,它往往被归类为混乱的症状-如果不是个人的症状,那么就是他们建立的社会的症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路:“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是家,所以最终人们渴望回到一个可以以某种方式回到家的地方,因为这是唯一一个人想要回到家的地方。”几乎从它最早的非医学考虑开始,怀旧就被认为是对现代状况的一种反应,是现代生活中混乱和陌生的风暴中的一个港口。哲学家、批评家和理论家仍在探索这一主题的变体,尽管作为批评理论的对象,怀旧已经逐渐失去了任何有意义的地域感(甚至可以说是时间感),并与真实性的概念和我们对真实性的追求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兴衰,怀旧的有用性和意义略有增加)。这就是鲍德里亚在“模拟与模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一书中观察到的一些东西的基础,即“当现实不再是过去的样子时,怀旧就承担了它的全部意义”:潜在的含义是,如果我们被某种意义上的真实淹没了,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回头寻找它--更不用说渴望回归了。
流行的观念花了一段时间才跟上文化理论家的脚步。乡愁作为一种观念贯穿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但直到五、六十年代,怀旧才真正开始渗透到大众意识中。乡愁既是概念,也是这个概念的首选术语。就像许多怀旧一样,它突然流行起来的确切原因是模糊和难以捉摸的:弗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在1979年对当代怀旧的研究中指出,即使在50年代,怀旧也被认为是一个“花哨的词”,仅限于专业人士和“有修养的外行演讲者”,但到了60年代,它的说法已经足够普遍,足以成为流行书籍和杂志考虑的主题。戴维斯提到的一种理论是,随着“家”的概念变得不那么强大-随着人们更频繁地四处走动,更容易获得更广泛的信息来源,变得不那么专注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想家的力量失去了一些,怀旧作为一种捕捉同样感觉而不被束缚的方式悄悄出现:从本质上说,怀旧成为了它试图描述的感觉的更好隐喻。家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时间,而不是一个地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词来形容它。
虽然数字时代增加了另一条皱纹,但还是或多或少地保留了现代怀旧的概念。随着文物和过去的表现变得更容易获得,怀旧逐渐成为一种更活跃的过程。经典地说,怀旧最好理解为某种偶然性,由一些意想不到的邂逅引发的匆忙--普鲁斯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