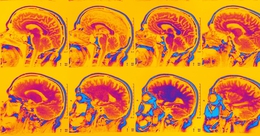灾难“准备”曾经是美国人的一种消遣方式。今天,它再次成为主流
做好最坏打算的人喜欢谈论僵尸启示录,这是有原因的。罗曼·拉日夫斯基(Roman Zrazhevski)说,一支行尸大军充斥着整个国家的想法弥漫在他们的脑海中,因为“如果你像僵尸末日即将发生一样做好准备,你就有了所有的基础。”这意味着:一条逃生路线,医疗补给,几周的食物。
兹拉日夫斯基几十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几个月后,他出生在俄罗斯。在餐桌上,他的家人经常谈论这场灾难和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在他们搬到纽约后,2001年9月11日,萨拉日夫斯基站在布鲁克林高中外的海滨,看着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即使在那时,他也准备了一个小行李包,里面装着救灾物资。
现在,他是那种每次场合都有装备和清单的人,包括带他的孩子去海滩。Zrazhevski住在德克萨斯州,经营着救生装备公司Ready to Go Survival和Mira Safety。2019年,随着香港的抗议活动、澳大利亚的野火以及与伊朗开战的威胁,商业蓬勃发展。但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去年1月宣布美国首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时,Zrazhevski说,业务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他的公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在争先恐后地完成延交订单。蜂拥而至的新客户提出了如此多的问题,以至于他雇佣了7名全职员工仅仅是为了回复电子邮件。“这有点像是客户服务的噩梦,”他说。“人们真的疯了。”
在真人秀节目引发的公众想象中,准备人员是孤独的生存主义者、狂热宗教团体的成员,甚至是购买豪华地下掩体并为逃亡的直升机加油的硅谷富豪。但在现实中,准备工作的人既有纽约人,他们在工作室公寓里挤着额外的罐头食品,也有荒野专家,他们的掩体储备充足。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八个月后,当我们回忆起空荡荡的过道和医疗用品短缺时,我们的集体心理发生了一些变化。枪支销量上升,烘焙面包和罐装面包成为时尚,厕纸库存也很常见。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吗?
冠状病毒大流行是预备者所说的“击中粉丝”事件的缩影。随着国家准备迎接封锁,并在去年3月开始出现关键供应短缺,人们发现自己悲哀地毫无准备。但在美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更多的平民做好了应对灾难的准备。
1979年,亚历克斯·比特曼(Alex Bitterman)上二年级时,玛丽·简修女(Sister Mary Jane)把她的学生聚集在天主教学校的体育馆里。她面前坐着一个三英尺高的灰色桶,她让学生们猜猜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们认为是小丑。还是蛇?修女打开箱子,拿出一条羊毛毯、一个塑料水罐和一大罐盐水。她说,如果苏联在纽约的切克托阿加镇投下一枚核弹,这些物品就可以拯救他们。
几十年来,这样的桶对美国小学生来说并不令人惊讶。比特曼学校体育馆的后面有一堆储备,行政办公室的一个黄色活页夹里放着一套针对各种灾难的超本地化应急预案。因此,当新冠肺炎来到美国时,现在是纽约州北部阿尔弗雷德州立学院(Alfred State College)建筑学教授的比特曼(Bitterman)记得那个桶。他研究极端事件是如何塑造社区的。41年后,他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集体准备。“为什么我们坐在家里等着有人来救我们?”他说。“没人会来。”
但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国家感到有人会来。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催生了新政(New Deal),它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网--社会保障、联邦住房和联邦失业保险--并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当他们需要帮助时,政府会出手相助。帮助他们为灾难或袭击做好准备是交易的一部分。
1941年,在二战期间德国轰炸期间,美国人看到英国平民在伦敦地铁避难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成立了民防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Defense),目的是帮助美国人为地方层面的军事攻击做好准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期间,政府授权的各种民防机构一直在运作,为社区提供指导方针和资源,使应急响应保持在当地。
这一努力体现在比特曼从小就记得的木桶和活页夹中,以及国家紧急警报系统等东西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指定的民防电台频道将在苏联袭击的情况下广播信息。几十年来,每家电台和电视台都被要求每周测试该系统。民防圣经--162页,由政府发布的“蓝皮书”--制定了应对紧急情况的战略和指示,往往将责任停留在超地方性。作者强调,家庭单位是“有组织的自我保护的基础”。很快,从建筑(地下室防空洞)到教育(臭名昭著的课堂“躲避和掩护”演练),需要做好准备的意识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十年后,古巴导弹危机再次敲响了警钟。比特曼说,从距离海岸90英里的地方瞄准美国的核武库削弱了美国不受外部威胁的想法。该机构的名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民防适应了20世纪不断演变的威胁。比特曼说,这是“我们共同的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我们有一个统一、协调的努力,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灾难做好准备。”
随着冷战的解冻,自然灾害的威胁接踵而至:东海岸的飓风,中西部的龙卷风,加利福尼亚州的地震。这些问题太大了,当地社区无法单独解决。大规模的环境污染需要联邦政府进行清理,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反应堆熔毁等灾难吓坏了公众。
民防办公室似乎不再重要,部分原因是他们推广的方法已经被认为是可笑的。在核攻击中躲避和掩护?人们开始怀疑这些演习是有效的,还是仅仅是宣传。1979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解散了民防办公室,转而成立一个集中的灾难管理机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
但一系列管理不善的灾难应对措施,特别是1992年的安德鲁飓风和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导致一些美国人对联邦应急管理局失去了信心。进入现代的准备者行列。
“你可以相信街上的鲍勃或简警官,但谁知道这些人是从华盛顿来的呢?”比特曼说。他补充说:“联邦应急管理局演变的一个奇怪之处在于,它的庞大规模引发了不信任。”“这是催生准备运动的催化剂的一部分。”
大约两年前,安娜·玛丽亚·邦兹(Anna Maria Bound)开始在哈莱姆区的一座教堂参加纽约市预备者网络(New York City Preppers Network)的月度会议。在一次典型的会议上,与会者讨论了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应急计划。在周末,他们会进行短途旅行:邦兹学会了生火、过滤水、提供基本的急救,以及探索从曼哈顿出发的最佳徒步逃生路线。
邦兹是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社会学助理教授,当时他正在研究一本关于城市预备者的书。她注意到,大多数成员都是有色人种,还有许多是家庭成员。她说,当卡特里娜飓风等灾难清楚地表明,白人和富人在危机中会得到更好的服务时,他们就加入了。冠状病毒大流行强化了这一观点。
金钱可以用私人医疗、远程工作和杂货快递的形式买到安全,或者-就堪萨斯州农村一个数百万美元的生存社区来说-与前海豹突击队保安一起在退役的导弹筒仓里买一套公寓。主要来自少数族裔社区的基本工人没有这种保护。在美国,非裔美国人、拉丁裔和其他有色人种都受到了冠状病毒的不成比例的打击。
“这场流行病暴露了阶级之间的不平等,”邦兹说。“预科的问题是,当我们看一看阶级划分的时候,它只是放大了已经存在的东西。非常富有的人已经选择退出集体体验的许多部分--这只是另一个例子。“。
在预备会议上遇到的人们并不是在囤积军用物资的掩体--他们在REI和Costco购物,通过在亚马逊上找到的书籍学习诀窍。即使在大流行之前,Pottery Barn和Nordstrom也在销售奥普拉(Oprah)和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推荐的洛杉矶初创公司Preppi的救生袋。但是,如果准备工作的主流程度可以用一个时刻来衡量,那可能是在2月份,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向她的1.79亿Instagram粉丝发布了一张戴着N95面具、戴着橡胶手套、带着一个标有朱迪(Judy)的橙色小袋子的自拍。她写道:“多亏了@ReadysetJudy,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旅行准备。”
Judy是一家备灾公司,由西蒙·哈克(Simon Huck)创办,他作为卡戴珊(Kardashians)等明星的影响力大师已有近20年的历史。在创办朱迪两年后,也就是2020年1月27日,他推出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生存用品,包装在明亮的橙色包装中。他的时机是偶然的。他现在说:“很难找到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
在两个月内,流行病和卡戴珊在Instagram上的喊叫的强大结合使哈克的销售额增加了两倍。他的绝大多数客户都是第一次做准备。在工具箱中,哈克包括了24小时专家热线的号码。任何人都可以输入他们的邮政编码,每周收到几条短信,上面有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具体地点的建议和数据。目前有超过4万人订阅。“作为大流行期间的应急准备品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哈克问。“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提供信息。”
像朱迪这样旨在提供备灾信息和设备的服务机构并不缺乏。几乎每个州的生存学校都教授离网生活、宅基地和荒野技能。美国预备营在阿巴拉契亚山脉提供为期三天的课程和露营。像盐湖城的PrepperCon这样的大会通过演讲、摊位和课堂培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但很少有这些节目能接触到主流观众。
当前的健康危机是否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们购买食品杂货、上学和通勤的方式?或者一旦疫苗上市,我们会不会回到我们的旧习惯?就像冷战时期的地下室防空洞和9·11事件后的机场安检一样,我们周围的物理空间将会适应。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天衣无缝地融入我们的生活背景。准备工作会在其中吗?
“我认为准备工作会一直持续下去吗?”询问界限。“”当然可以。但我认为,它已经成为主流,但也有耻辱。人们并没有谈论这件事。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