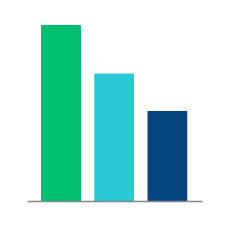我在Scala社区的性骚扰经历
“唯一对邪恶胜利所必需的唯一作品是为了好的[人]无所事事。”
经过三年的沉默,我决定通过Scala社区的崇拜图,分享我在过去几年里被操纵和骚扰过去几年的故事。
三年前,我是21岁的本科大学生,他是对Scala热烈的,并希望参与其周围的社区。然而,作为非母语英语扬声器,我被吓倒和不愿参加了Scala会议。 Heather Miller是我大学的教授,以及一个着名的Scala社区领导者,鼓励我参加,并在2018年参加了我在Nescala的第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Jon漂亮。
乔恩漂亮是我在社区中遇到的第一个人之一,他通过在Twitter上突出显示我来迅速获得了我的信任,将我与社区中着名的开源维护者和有影响力的人物联系起来。他告诉我,他向我推荐了接受我的谈话的会议,这让我相信他是我被选为发言人的原因。我相信他是一个导师和一个亲密的朋友,相信没有他,我无法如此迅速加入社区。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还提到了几次,他帮助其他女性参加会议,以至于他们无法与他们分享航空公司以减少其旅行费用而无法参加的会议。他问我是否想在柏林的Typelevel会议上分享Airbnb。他还提到他计划邀请别人。作为财务资源有限的学生,我接受了诱人的报价,感到不满,再次,他帮助了我。起初,他提到我可以邀请别人加入我们的航空公司。只参加了两个会议,我当时不了很多人。当我想到一个人来邀请时,他阻止了我,问我是否没有感到舒适地在与他一样睡觉,如果我试图为我们获得陪伴。我感觉不好,我让他感到不受信任并停止要求其他人加入。
当我抵达柏林时,我发现航空公司失去了行李,我的电子产品在没有充电器的情况下死亡。我被外国人滞后,疲惫,沮丧,迷失方向。我饿了,因此买了一些食物。记住他建议我在之前的谈话中得到牛奶和葡萄酒,我也买了它们。我不记得我喝了多少钱。我不记得他喝酒。但是当他对我的进步时,我记得感到不舒服。当我陶醉时,我觉得正在利用他与我无保护的性行为。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我记得恐慌和哭泣。
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觉得他是一个对象的对象。例如,他在会议上致散我,但希望在Airbnb中亲密。还有另一个时候,他坚持有不管我说我不想的话。我没有责怪他发生的事情,并不认为这些行为当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甚至不穿过我的想法,他会做任何我不舒服的事情。我相信他不会伤害我。我甚至归咎于自己不清楚。
我在那个时候感到不知所措,情绪强调,我向他提到的是,我想向父母联系以获得支持。他通过说我的父母无法帮助我,因为他们在一个不同的国家,我劝阻我。我觉得惭愧,孤立,害怕。
6月,希瑟注意到,在萨克拉地区之后,我在晚餐时感到不安。我和她分享了发生的事情。她警告我留在乔恩漂亮。她不是唯一一个告诉我的人。尽管我在柏林的经历是可怕的,但我很难接受那些似乎是一个好朋友,导师和盟友的人,可能是如此自私,操纵和残忍。
我在5月后与他保持友谊,因为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一致的,我不想“制作一个大场景”,就像他指责我一样。另外,他让我不要在这一集上居住。作为一个来自父权制文化的缺乏经验的年轻女性,我逃离了被认为是“传统”被认为的刻板印象。我应该,就像他暗示,并希望“很酷的事情很酷”。我缺乏识别来自性互动的滥用行为的知识。也许我缺乏经验,或者也许他在令人信服的人时也经历过。
我很愤怒地使我的记忆失效。他所呈现的故事总是与我所记忆的总是不同的。例如,当我对柏林的剧集面对他时,他告诉我,我诱惑了他。他的话让我害怕,羞辱和羞愧。我发现自己自己是自我怀疑,苦恼,沮丧。
甚至几个月后,我继续患有压力和恐慌的攻击。我开始治疗课程。从与我的治疗师交谈时,我开始认识到掠夺性,气候和辱骂行为。当我与朋友和家人分享我的经历时,他们都告诉我远离他。
我开始反思我的经历,并开始了实现发生在我身上的旅程。我以各种形式的沟通表达了几次,我希望不要与他进行更多的对话。他的存在,在线或亲自,使我造成很多痛苦,压力,甚至伤害。我的界限不断被侵犯。他继续在不同的谈话中吸引我,“情绪上拖息”我(用他的话说),并公开召唤我并暗示自己进入我的空间。以下是一些事件(但不是全部):
他提到他不想让我停止与他交谈,因为他认为我“可以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和有价值”,他有很多东西要提供。我感到精神上和身体威胁。
在2018年湾的规模,Seth Tisue和我在一个小摊位上进行了谈话,乔恩很漂亮地阻挡了门,并指向对话给不同的话题。在我走开之前,我坐在那里被迫听到他说话。我害怕表现出任何负面情绪,因为我可以被视为疯狂和不合理。
会议结束后,他加入了一个小组晚宴,我计划提前参加。因为他的存在引发了这么多可怕的回忆和情感,我在洗手间前面闯入了厕所前面。帮助我安排我早晚晚餐。
他迫使我在2018年兰姆达世界拥抱他。他说他知道他不会遇到麻烦,因为我也拥抱了其他人的朋友。
在Nescala 2019年,他被登记处停了下来,我正在帮助Brian Prapper,并试图和我说话。看着别处我忽略了他。
在2019年湾的规模,阿德尔伯特·张和我坐在午餐时坐在一张桌子上,走向我们。阿德尔伯特是我与发生的事情分享的朋友之一。知道我不想让他接近我,阿德尔伯特让他聊在别的地方。
回顾一下,我们的谈话中还有时间,他提出了问题的评论让我感到不舒服。他吹嘘我在Scala社区与至少十名女性的密切互动:咖啡,日期,亲吻和性别。我发现在许多这些故事中,几乎总是女性被他迷住,“非常喜欢他”(以他的话说)。了解他如何描述我们的情况,并了解自恋和散装,我有理由不相信他与这些妇女的互动的特征。我以前在会议上遇到过其中一些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适合:年轻,新的技术或社区,非母语英语扬声器,拥有少数背景(种族,教育,财务......),缺乏性或辱骂行为的知识等。
我已经向2019年报告了我对屠宰场的所有经验。我希望看到建设报告机制等具体行动,以保护社区中的少数群体。不幸的是,我不知道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我没有在公共场合发表讲话,因为我相信他是在社区中的强大,权威,有影响力的,并且很受欢迎,并且他将很容易地摧毁我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此外,社区中的许多人认为他是朋友,没有人会相信我和我的经历。
一个月前,我看着纪录片,肮脏的富裕。而且我绝对是敬畏的女性,如莎拉·勒罗姆和艾米麦克里·麦克里,他们站起来绑架,无论施工者的权力如何。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他们保护他人的决心。此外,与VIC联系并学习与JON漂亮的类似经验让我意识到我并不孤单。了解最近举办社区中更多的女性,我意识到这种行为永远不会停止,如果人们不知道。
今天,我在说话。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来获得声音,我不会沉默或再次吓倒。我不是想说服任何人。我只是想分享我的故事并与我的创伤经验和平。也许通过发言,我可以把我的被盗的力量带回。也许,我的故事将帮助人们了解掠夺性和辱骂行为。也许,我可以帮助防止下一个女人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