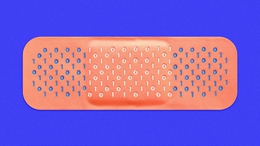作为“锁定”患者的内心生活
杰克·海恩德尔(Jake Haendel)是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昏昏欲睡地区的主厨。当他28岁时,他的海洛因成瘾导致了灾难性的脑损伤,几乎杀死了他。在短短几个月内,杰克(Jake)的存在变成了头脑中的声音。
杰克年轻时的父母已离婚。他在波士顿遥不可及的两个小镇的两个房屋之间长大,只不过是脱衣舞厅,生病的教堂和半空的运动酒吧。他的母亲在19岁那年死于乳腺癌。那时,他已经卖了大麻,并滥用了阿片类药物OxyContin。 “就像我学校里的很多孩子一样,我爱上了氧气。如果我要和家人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我会去洗手间只是为了解决问题,”他说。他开始烹饪学校,在那里继续尝试阿片类药物和可卡因。他在社交,爱好娱乐的阵线后面,将家人和朋友的毒品隐藏起来。在里面,他感到焦虑和空虚。他说:“我麻痹了参加聚会。”
烹饪学校毕业后,他在当地的乡村俱乐部当厨师。 25岁时,杰克(Jake)首次与同事一起尝试使用海洛因(众所周知,麻醉品在美国厨房中非常普遍)。到2013年夏天,杰克(Jake)努力寻找处方阿片类药物。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抵制阿片类药物戒断的症状,他将其比作“严重的流感病例,有一种即将来临的厄运感”。海洛因情绪高涨,避免了剧烈的恶心和颤抖的退缩。
尽管上瘾越来越严重,杰克还是在2016年底与女友艾伦(Ellen)结婚。在恋爱初期,艾伦问他是否正在使用海洛因。他毫不犹豫地撒了谎,但她很快就发现了真相,几个月后,婚姻破裂了。他说:“我一发不可收拾,卖了很多海洛因,甚至使用了更多的海洛因,花了可笑的钱购买毒品和酒精。” 2017年5月,艾伦(Ellen)注意到他在开玩笑,说话含糊不清,音调偏高。 “你的声音怎么样?”她反复问他。
5月21日,一名公路巡逻人员在杰克上班的路上拦住了他。他不规律地驾驶,在车道之间加速和转弯。那天早上,他按照自己的常规作法,抽着海洛因,然后才刷牙。他开车时抽烟或“游离碱”海洛因,在箔片上加热粉末并吸入烟气也是正常的。他告诉我:“我实际上很擅长此事。”当警官走近他的汽车时,杰克可能感觉到他的身体有些不同。他需要掩盖海洛因袋,该袋袋在中控台上可见,但他无法伸手将其关闭。他的手臂毫无用力地朝仪表板挥了拍。警察以管有毒品为由逮捕了他。
杰克保释,但几乎不能走出车站。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的病情恶化,5月24日,他的妻子给他们的家叫了一辆救护车。他跌跌撞撞地走到前门,靠在墙壁上以支撑自己。医疗人员认为他可能中风了,所以他被送往医院。脑部扫描显示出明确的成像模式:对白质的深远,双边损害,即促进大脑不同区域之间交流的神经纤维束。
他被诊断患有中毒性进行性白质脑病,也被称为“追龙综合症”,通常是由于吸入加热在铝箔上的海洛因烟雾所致。一种未知的毒素,可能是在海洛因中添加的某种物质,可以使它进一步发展,正在对杰克的大脑造成严重破坏。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或治疗方法,因此他被送回了一家姑息药商店。
在整个夏季和秋季,杰克的症状都恶化了。他的肌肉变得虚弱,四肢扭曲了。在家里,他经常摔倒,吞咽困难。他不能吃固体食物,讲话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
去年11月,杰克(Jake)被送进医院,并转移到神经科学重症监护室,在那里他被戴上了呼吸机和饲管。他遭受了自主风暴-脑部受伤后有时会出现的令人恐惧的症状。在暴风雨期间,神经系统处于过度活跃,受干扰的状态。血压上升,人体大量出汗,剧烈痉挛,呼吸迅速而浅浅,每分钟心脏跳动200次以上。杰克一次要暴风雨四,八,十二个小时。 “看着真令人痛苦,”他的父亲,他是一个60年代初说白话的人,对我说。
杰克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他感到害怕,困惑,有时产生幻觉。髓磷脂的损伤,即大脑神经细胞周围的保护鞘,一直发展到他无法控制运动,既无法讲话也无法指导眼球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无法交流。他可以听到护士和医生的评论,他们认为他受到了不可逆转的脑损伤。杰克回忆起一位急诊医生正在观察他,就像要解剖的标本一样。 “哦,天哪,这个家伙太合同了,”医生说着,盘旋在杰克脸上上方几英寸处。杰克告诉我:“听到他这样说我,我感到更加痛苦。” “就像我不在那儿一样。”
最终,暴风雨的程度有所减轻,他被转移到了疗养院。一段时间后,他在家中得到姑息治疗,这通常是给那些患有绝症的人。父亲被告知杰克有望在几周内死亡。
对于外部观察者,杰克没有表现出任何知觉或认知的迹象。 “他在里面吗?”他的妻子和父亲会问医生。没有人确定。他的大脑的脑电图(EEG)显示神经活动模式中断,表明严重的脑功能障碍。 “杰克几乎就像一个室内植物,”他的父亲告诉我。
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杰克是有意识的。从医学上来说,他被“锁定”:他的感觉完好无损,但他无法交流。
杰克后来写道:“根据工作人员将我放在床上的位置,我只能听着什么,只能看到我面前的直接区域。”该疾病袭击了通过大脑和肌肉传递信息的电缆,但没有进行有意识处理的区域,因此他完全警惕了自己的处境。他努力地理解了这个新现实,无法沟通,并且对这种孤立永远存在的前景感到恐惧。
在整个过程中,Jake保持清晰的自我意识。他感到每一次颠簸,缠绕和痉挛。他后来写道:“我无法告诉任何人我的嘴是否干燥,是否饿,或者是否有痒的痕迹。”
他一直在痛苦中,并且害怕死亡-但更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永远被困在体内。
几个月来,杰克除了听自己的想法之外什么也没做。他的病情与法国记者让·多米尼克·鲍比(Jean-Dominique Bauby)的情况相似。他在1997年出版了一部回忆录,讲述了他的锁相综合征的经历,由抄写员解释鲍比左眼睑的眨眼。标题,《潜水钟和蝴蝶》,让人联想到他的身体像是一个下沉的坟墓,上面挂着一个氧气罐,他的大脑是一个飘动的生物。 2007年,该书被制作为获奖电影。
从那时起,医学专家就发明了与锁定患者进行通信的方法(包括突破性的“脑部读取设备”)。他们还对锁定的患者的精神状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研究表明,令人惊讶的数字表明他们的生活质量很高。就鲍勃而言,在这样令人痛苦的经历中努力寻找意义。他的回忆录是沉船事故的惊人画像。鲍比写道:“不仅我被放逐,瘫痪,沉默,半聋,被剥夺了所有的享乐,还沦为水母的存在,但我也感到震惊。”
“我一直都感到恶心,”杰克告诉我。他通过导管接受氧气和食物,并且不断地流汗。他的皮肤对轻微的感觉变化敏感,经常被烧伤。自主性风暴虽然不那么严重,但仍在肆虐,夹住杰克,令人心痛,心跳加速,高温和令人窒息。
回到家里,杰克的世界缩到了低矮的房间里。卧床几个星期后,他发生了某种内部来回回响,这成为他生存的关键。当他后来描述他经常疯狂的内心对话时,“两个声音,都是我自己的”。
“是的,它很快就会到来。不要惊慌。没关系。”
“我知道,我正努力不让自己害怕。哦,天哪,我吓坏了吗?我怎么了?”
杰克的需求很多而且持续不变。护理人员,护士和艾伦(Ellen)–转向他以避免痛苦的褥疮,让他被子盖住,并通过他的管子挤挤止痛药和流食。尽管他们不知道,但杰克也与他们进行了许多“对话”。
“人们在我周围聊天时,我会一直插话。如果一个护士问另一个人,“他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我会大喊:“是的,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杰克继续说:“我爱任何人都可以跟我说话,即使他们没有我真的不相信我在那儿。一位助手向我唱歌。另一个人说:“杰克,你看起来像希腊神。”我承认我是那样的。
Ellen比任何人都可以肯定自己已经完全意识到了。她有能力看着他的眼睛,了解他的需求。他称她的直觉是“心灵感应”。比利时神经病学家和锁定综合征专家史蒂文·劳瑞斯(Steven Laureys)表示:“事实证明,超过一半的时间是首先由家人而不是医生意识到患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医学专业人士确实提醒家人“看他们想看的东西”。
就杰克而言,他回到家后,大多数家人和朋友都很少被告知他的健康状况。艾伦(Ellen)高度保护他,将他与潜在的“不良影响”隔离开来,并坚持认为他只会偶尔接待游客。
杰克无奈地目睹了他躺在房间里的激烈争论。他只能直视前方,因为关于他的照顾的痛苦行在整个房子中回荡。今天,杰克和他的妻子疏远了,不再交流了,但是他仍然被锁定时将她视为自己的生命线。
后来,一名心理学家告诉杰克,他的持久意识是“礼物和诅咒”。杰克说:“我非常想告诉所有人我在想什么。”他忍受着极大的罪恶感,因为他是一名吸毒者,使他的家人经历了一场噩梦般的磨难,而且该州不得不负担一笔非常昂贵的医疗费用,可能要花费数百万美元。
除了不断感到不适和羞耻外,他压倒性的感觉是几个小时的缓慢爬行。 “该死,无聊!”他说。他脑子里解决了数学问题,并且幻想着在户外,玩游戏,做爱。他一遍又一遍地算出了1,000秒。
在他养老院的房间里,墙上的时钟挂在视线之外。他告诉我:“那就像是折磨。”电视不仅可以娱乐,而且可以作为时间追踪的手段,提供慰藉。杰克弄清楚了什么网络电缆显示在哪一天晚上出现。杰克说:“我一直想知道现在几点,今天几点,多长时间。”
然后是清晨繁荣的传教士。大多数时候,杰克在凌晨5点到早上7点之间会流汗。那时,廉价的时候,福音传教士经常出现在本地网络上。杰克(Jake)鄙视他们的历史性杂音,但别无选择,只能听他们说话。他后来在Facebook帖子中写道:“我每天早上都必须听宗教信仰的要钱。” “我感觉自己像在地狱里,就像我已经在遭受折磨一样,这些骗子艺术家在折磨之上是折磨。”
杰克(Jake)在这段时间非常沮丧,“思考很多令人沮丧的想法”并反思过去。 “有几天我会考虑几个小时的葬礼。”
六个月后,杰克(Jake)的寿命超过了该州的预期寿命,并且无法再接受家庭姑息治疗。医务人员仍然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识,但是他的生命体征足够稳定,可以动弹。他于2018年5月入住波士顿麻萨诸塞州综合医院进行重新评估。
再入院的几天里,杰克开始对生存甚至恢复感到越来越希望。
在6月下旬,他注意到他可以对视线施加非常有限的控制,仅足以上下移动视线。杰克说:“我心想:‘这是新的’。”控制视线注视可能是恢复非语言交流的第一阶段–但起初并不一致,因此尽管工作人员注意到他的眼神闪烁,但仍无法确定他是否在有意识地引导他们。 “听到医生的一遍又一遍的“那是非自愿运动”实在令人沮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内部歇斯底里地哭泣,”杰克告诉我。
他的父亲说:“杰克脸上没有表情。” “很难想象他在那里。”
2018年7月4日,杰克取得了突破。那天晚上,杰克从医院的22楼可以听到但看不到查尔斯河上空的独立日烟花。他说:“我心想:‘我会再次看到那些东西。’
第二天,杰克(Jake)的初级保健医生发现右手腕非常轻微的运动。他飞到床头。他的医生说:“如果可以的话,再做一次。” “动动手腕。”
杰克突然发现他不必考虑这一点。他的手腕只是动了动。动作不大,但是这表明他的身体正在醒来。他的医生大为震惊。杰克感到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
几天之内,他设法眨了眨眼以回答问题。一周后,他被转移到全镇Spaulding康复医院的脑损伤病房。 Spaulding是一幢令人印象深刻的设施,位于一幢时尚的现代建筑中,经常被评为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
在随后的几周中,杰克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对自己重复一连串肯定的短语-“您可以做到”,“您会做到”。他说:“我只是真的想变得更好。”经过努力,他开始动动脖子和舌头。杰克告诉我:“我非常兴奋。”很快,他实现了一种粗略的交流系统:表示“是”,说“不”,眨眼。
Spaulding的言语治疗师Michelle Braley惊讶地与一位先前被认为是绝症的患者一起工作。 “当我阅读他的图表时,我记得在想,‘这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案例,它成为了康复的候选人。”
布雷利(Braley)帮助贾克(Jake)从一个简单的信笺板开始学习非语言交流。随着杰克(Jake)对视线的控制越来越强,布雷(Braley)为他带来了一种名为MegaBee的设备,该设备可让患者使用眼球运动来选择字母和短语,然后将其显示在屏幕上。杰克经常哭泣,拼出了第一个信息,然后提出了困扰他几个月的问题。
“ A ... M ... I ... S ... T ... I ... L ... L ... G ... O ... I ... N ... G ... T ... O ... D ... I ... E,”他在Spaulding的物理治疗师丽贝卡·格拉斯(Rebecca Glass)问道。早期的MegaBee会议。
她从MegaBee的屏幕上抬起头。她说:“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杰克,我不这么认为。”
大约在这个时候,埃伦每天仍在访问。她一直坚称他仍在那儿,现在杰克终于可以表示感谢。
一旦他可以交流,医院工作人员就可以评估他的进度。布雷利说:“我进行了一项认知评估,看是否因白质脑病而导致了损害。” “到那时,我意识到杰克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再次,工作人员震惊。他们怀疑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知道的,但是杰克可以清楚地回答每一个问题-有关他的状况,他的过去。
在创伤或进行性疾病后,大脑如何自我修复仍然是个谜。不过,在最近几十年中,科学家们了解了更多有关如何形成新的神经回路以及如何“招募”大脑的不同区域以恢复失去的功能的知识。
我问Spaulding的脑损伤专家Seth Herman,像Jake这样的人如何康复。他列举了大脑将功能转移到不同区域的能力。他说:“大脑想要愈合,改变自身并形成新的神经通路。” “重复是关键,杰克愿意投入工作。”
一支由物理和职业治疗师组成的团队花了几周的时间来操纵杰克的肌肉,并使用石膏来重新调整他的四肢并改善其活动范围。收益不高,但意义重大。自主风暴随着时间而消退。杰克变得更强壮。
Jake于2018年9月离开Spaulding,并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医院继续康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仍然局限于床和轮椅上,但是他又在移动,与人互动并获得信心。到2019年春季,在接受深度治疗后,他再次讲话:首先是元音发音,然后是简单的短语,例如“我爱你”和“谢谢你”,然后是完整的句子。他与几个月来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的家人和朋友进行了视频通话,欣喜若狂地说:“惊喜,我还活着!”
在杰克(Jake)在Western Mass期间,艾伦(Ellen)越来越远。到了夏天,她已经停止拜访了。 2019年5月,杰克(Jake)为挽救这段感情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组织了一次电影约会。一位休闲治疗师将他送上货车,带他去附近的电影院。艾伦在那儿遇见了他,治疗师将这对夫妇安置在一个空荡荡的行中,让他们独自一人。他们观看了《突破》(Breakthrough),这是一部2019年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从昏迷中康复的故事。他们在观看解体和恢复的场面时牵手。他们俩激动地离开电影院,并同意当晚晚些时候进行视频聊天。但是他说她没有接听电话,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
锁定综合征很少见–据估计,在任何时候,美国只有数千人。大多数患者是中风或脑外伤的受害者,极少恢复明显的运动功能。
杰克(Jake)是从锁定状态中脱颖而出的少数人之一,医生们将他的康复描述为“显着”和“独特”。尽管MRI扫描继续显示出大脑白质受损的迹象,但他已经恢复了言语能力,并希望很快再次行走。
我今年2月在Tewksbury医院遇到了杰克,这家医院位于波士顿郊外一座老旧而严厉的医院。自从他恢复交流能力以来已有18个月了,而且,正如他通过短信告诉我的那样,他的讲话在最近几个月中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在漫长而无菌的走廊中导航到一堵粉红色墙壁的房间,他独自坐在其中,直立躺在床上,渴望说话。
尽管他的四肢仍然紧缩和僵硬,但杰克却颇具生气,通过淡褐色的眼睛和张开而又宽容的脸庞展现出一种强大的性格。他和我都快到30岁了。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好吗,伙计?”
他的快乐使我大吃一惊。他对自己的新笑容保持清醒的意识–生病之前,那是深沉而响亮的;现在它的音调和呼吸很高,但即使描述最黑暗的时刻,他也一直咯咯笑。他的讲话语气缓慢,曲折,并发誓要解除武装,脚踏实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