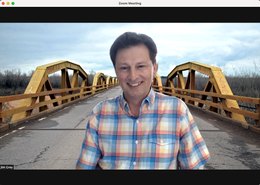实验室文化:面试匿名生物学家(2019年)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使科学家允许使用前所未有的精度和速度进行修改遗传码,并且在成本的一小部分中。这一直是改变生物学研究的游戏。科学家现在可以在可能之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科学家进行对遗传密码的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科学发现在受欢迎的新闻中获得嗡嗡声以及科学家自己兴奋的是往往是相当不同的。所以我们很想了解有关科学家如何看待这些发展的更多信息。更基本上,我们想知道研究的坚果和螺栓:实验室如何运作?谁在他们身上工作,阶层是什么样的,这笔钱来自哪里?关于科学研究的道德的对话如何与科技世界中的谈话不同?在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前景在生物学中有博士学位的人在那里出现在那里?
在我们的厨房桌子上喝饮料,我们坐在细胞生物学中的当前博士学生来了解更多信息。
您以前作为一家大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曾担任硅谷。您是如何决定成为生物学博士学生的?
我记得终于在我正在阅读这个理查德Dawkins书籍,祖先的故事中达到了决定,这是对生命之树的探索。它从人类向后工作,并试图找到我们的共同祖先,其中包含所有存在的其他生物。我一直在享受这本书和所有关于生活的小插管,忽略了他偶尔的咆哮,了解为什么上帝已经死亡和所有这些。最终,他到了细菌,我开始超越他对细菌和病毒和古老的所有事情以及什么。
它达到了我在公交车上随意的对话的地步谈论我正在阅读的东西,而且它在我身上恍然大悟,我对生物学兴奋的方式,这种方式与我对我的工作感到兴奋的方式截然不同当时。我在一个学科中遇到了一个我要解决酷问题的纪律,但我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与物理世界进行。
为了理智 - 检查我想要改变职业的愿望,我做了与生物学家的信息面试,以了解可能会让我在日常工作中触摸这东西的可能就业机会,以及我需要做的事情让我的手放在舵手上。
很快就是清楚地对生物学领域的事情之一是人们通常对基本问题的答案,但有一大吨问题没有人有答案。当我问一个更深入的后续问题时,他们可能会答案。然后,当我走一个水平时,他们就会喜欢,“哦,是的,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最终,很明显,我真的需要有一个博士学位,以便让我最想要的谈话,所以我最终追求了这一点。
这很有趣:当我在申请文章的第九次迭代等事情上时,我坐在手机上,在咖啡馆里,在特派团试图向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转变为生物学,并努力时间上升了一个凝聚力的联系。但她就像,“这是完美的感觉。当你十分之一时,你对纳米技术感到兴奋,谈到你将如何让你的牙齿清洁牙齿,现在你正在以同样的方式谈论细菌。“
如果我不得不追踪共同的线程,那将是在我们习惯甚至适用的物理学的范围内互动的微小代理人的想法 - 这是一个考虑的超级令人兴奋的世界。
所以现在你是一个在研究实验室工作的博士学生。一般来说,你的工作看起来像什么?
我们研究细菌,所以我们结束了与想要预防传染病的人也相关的学习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病原体实验室;我们没有专注于预防传染病。我们当然与实验室合作 - 正在研究药物和抗生素的那些,或者研究病原体并试图了解他们的生物学。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细菌中的基因集合,当你删除它们时,杀死细菌,”然后某人更直接地与病原体一起工作,“好的,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在细菌中除去这种基因功能的药物,其他在细菌中击倒这种不同的基因功能,他们都被FDA批准。“
发布研究论文时,我的实验室总是对我们所谓的“在论文中有生物学”非常感兴趣。如果你在纪律之外,我肯定的是,如果你在学科之外,这也意味着如果我建立一个新工具,我希望能够向你展示一个新的生物世界作品的新方法;我不想只是描述我建造的新工具。我们经常试图开发新技术,让我们对细菌进行稳健和精致的测量,然后阐明在这种微型规模处推动寿命的精美基因网的功能。当我们能够做到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很难理解细菌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通过看着它们来做。你可以看到这些小药丸形的东西,如果我们混淆他们,我们有时可以看到它们以有趣的方式死亡。但是,在我们可以观看细菌的水平,试图结论他们将是试图通过计算在巴黎在巴黎建造的国家古迹的数量来评估法国的福祉 - 你没有对个人人民的知名度或主要商品是或类似的东西。
所以而不是直接观察细菌,我们正在做的很多事情都在努力创造扰乱他们的方法,然后在大型的观测数据集中测量并记录他们的生活。我们希望这些数据充分差别,我们可以更加富有对我们在后来分析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然后为人们提供工具来研究各种细菌 - 致病或其他方面。人们使用细菌的各种目的,例如我们开发的许多技术可用于弄清楚更好的方法来获得细菌生产东西,无论是那种食品等酒精和酸奶等能量产品,如甲醇和乙醇,或酶像清洁洗涤剂中的酶。
但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只关心细菌如何做细菌,因为它从根本上迷人的是,这些微小的东西能够在周围的世界中幸存下来,在水中含盐浓度的轻微转变是这种大规模的生命或死亡发生在跨度,如三秒钟。它就像你的整个社区正在瞬间淹没。细菌只有一个计划来处理这一点。他们没有电脑,他们没有大脑 - 它们小于一个脑细胞或单个晶体管,但他们以某种方式实时地处理了一个行动,以实时处理该方案。
我发现那个迷人的,我认为这就是让很多人进入我所在的学科。在同样的事情是人体中的个体细胞都是如此,并且很多人“致力于癌症治愈”的人大多是对地狱中的令人着迷的是,这些蛋白质的细节是由内质子组装的网状物和高尔基体和其他。这种复杂的事情很复杂,在你的身体中每秒发生高约次。
你从国家卫生研究院获得资金的方式(NIH)是通过说“如果我们弄清楚,我们会更接近治疗癌症” - 并不让我错了,那些真正关心的人的一小部分在包括我的实验室的生物社区,是非微不足道的。很多人都喜欢生物学,我不知道,报复他们的祖父或其他东西。但对我来说,在细菌和人类之间的战争中,我可能会与细菌相一同。我不是真的在人类健康中。如果我能通过帮助促进这一点,我很棒,但我大多是好奇的细菌是如何做他们的事情。
就你现在正在做的研究来说,你在努力的最佳结果是什么?
我的实验室非常专注于基础科学,这就是说目标明确开放 - 这并不像我们要么找到特定问题或破产的答案。我们对重要问题有有趣的答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所以我们提出了新的方式来闪耀着那些黑暗的角落,然后希望我们找到很酷的东西。但我们并没有太过于终止那东西是什么。事实上,我们讲的故事,我们谈到我的博士工作在去年的情况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不是非典型的。
然而,实验室枢轴的研究课程的方式有点不同于启动可能枢转的途径。如果启动枢轴,它们正在将计划从一件事更改为另一件事。虽然在研究中,它更像是意识到你可以做一些以前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意识到我们过去遗弃的问题结果结果与许多其他事情相关。当这些发现发生时,你可以在新的方向重新聚焦,看看它需要你的位置。您需要敏捷以找到最佳成果。
所以我认为“最佳案例”取决于光线向我们指向我们的地方。
我最近听到的主要生物学是我们使用CRISPR的遗传码编辑遗传代码的进展,这有很多炒作。生物学家中是否以同样的方式炒作?它是否觉得是一个有潜力的真实的东西,或者是那么远?
Carrpr实际上只是“集群定期穿插短文重复”的首字母缩写。首字母缩略词意味着本身并不令人兴奋;这只是我们在DNA中看到的某种模式的占位符。
我们已经测量了很多人的DNA,但甚至更多的细菌和病毒。我们不知道它的大部分是什么,但识别基因比弄清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更容易。识别基因本身的界限相当容易,我们通常能够识别生物体的基因组的基本结构,特别是在原核生物中,如细菌,这些细菌在没有更复杂的遗传结构等内含子。我的意思是,细菌基因组仍然是具有代亚基DNA和转录调节剂的细菌基因组的相当数量的复杂性,但它无处可适用于像人类等生物体中的真核基因一样复杂。细菌DNA中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致力于实际转变为蛋白质的东西。
但在细菌基因组中,科学家们会发现这些模式,并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这种模式被赋予CRISPR缩写,基本上说:“我们在DNA中看到这种条刺图案,其中有一个重复的回文序列,然后它在重复的回文块之间有一堆其他东西,但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放在一起,在那些在病毒中发现的DNA似乎与病毒的指纹相匹配,在细菌的DNA中包裹着。
理解这一点来自酸奶制造业的突破。丹尼斯科是公司使Dannon Yogurt的公司,他们的业务的大部分是巨大的大桶的细菌,以使其酸奶。但他们的细菌会生病:有叫做它们的病毒称为噬菌体。如果噬菌体感染了一个在一个巨大的单血管增值税中的细菌菌株,那么该增值税的所有细菌都生病了。他们都搞砸了,你只需要一整件事。所有你投入批次的钱都走了。
所以Danisco是如:我们如何更好地识别它,何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并降低这些感染的频率?因为我们希望随着VATS感染的每次VATS都不会减少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乳制品。他们有一个研究司,正在研究酸奶细菌的CRISPR模式,以便更好地了解细菌的生病。它们在这种特殊的CISRPR模式中看到病毒DNA,并决定深入挖掘。
自从我看着原篇论文以来已经很久了,但他们基本上表现出他们在最终表现的实验,即抗病毒保护机制涉及Crispr。当研究人员用病毒感染细菌时,成功地争夺病毒的遗传方式以这样的方式改性,即它们的CRISPR模式随后含有纯粹的遗传引用,他们刚刚争夺了他们刚刚争夺的病毒。此外,没有保护机制的细菌对病毒的感染大大容易。他们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通用的保护机制 - 它是细菌中的反应性,适应性免疫系统。
让我们说你去你最喜欢的夜总会。后卫的弹跳杯与人的面孔有一个偏好的偏光板。当他走出前面并看到云雀克莱夫试图再次回到俱乐部时,他从宝丽来的墙上记住了克莱夫的脸,让他脱颖而出。
CRISPR模式基本上就像是偏光板的墙壁。事实证明,还存在与称为“CRISPR相关”或“CAS”蛋白质的模式相邻的所有这些基因,这些基因在其细节中变化。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Crisp系统和不同相关蛋白质的模式;它是一种完全精致的网络,被细菌用于病毒,对细菌的病毒,细菌对抗自己的病毒。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生态系统,但从根本上讲是这样的:你有一个细菌的免疫系统,站在那里时,作为一个弹药,可以在同一生物或不同的生物中抑制一些基因的生产,他们正在基于它在这个偏好的墙上,他们在开始转移时扫描。当发生新的病毒感染时,很多细菌都会死亡。但是那些设法幸存的人获得了几乎杀死它们的东西的快照,将它添加到墙上,然后在那个家伙出现的时候,他们可以就像,“没有克莱夫,你不能进来。“
人们早早实现,他们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应用这一点。它在分子生物学中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对于研究病毒和细菌的人来说,在学习关于细菌正在做什么和开发我们可以应用于其他生物领域的新工具的新工具之间建立联系。例如,有用的生化研究技术,如利用限制酶和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和连接酶......所有这些技术最终来自各种病毒或转座子或细菌,在那里我们发现一件事在某种情况下幸存的东西我们不会指望他们。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些正在发生的奇怪的分子器,我们可以复制。
谈到Carrpr,一些研究人员像UC Berkeley的Jennifer Doudna这样的研究人员在早些时候那里了解了进口 - 谁在那里找到了谁,谁应该得到诺贝尔或专利或其他什么 - 因为研究人员看到了,嘿,嘿,嘿,嘿,我们可以将Crispr与系统中的蛋白质组合使用,该蛋白质充当一对剪刀,这将允许我们使用组合系统在极具特定的地方开始切割DNA。
回到Bouncer类比,如果我想改变系统的行为,我可以向墙上添加新的宝丽来,而无需杀死保镖或更换他。我只需要潜入并添加新的宝丽来源,现在他不会让詹妮进入夜总会,即使詹妮从未做过任何错误。我刚刚对看到她不再被允许进入俱乐部时会发生什么感兴趣。以同样的方式,通过CRISPR基因编辑,您可以对DNA中的极其特定地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变化,努力很少。
这极大地减少了改变基因或击落病毒或蛋白质的遗传表达的金钱和努力。我们现在可以编辑靶向任意蛋白质,蛋白质负责细胞内部的大多数物理作用。因此,这对生物学家来说真的很令人兴奋,并且它正在改变替补席上的一切。
它获得公共嗡嗡声的是,在生物医学应用方面也潜在令人兴奋。我认为普通人对生物研究人员对大多数事情感到兴奋。新闻中有巨大的嗡嗡声,实验室里有巨大的嗡嗡声,但它们是关于不同的事情。他们重叠,因为有研究人员对您最终能够使用Crispr以切割将禁用癌症的基因的事实,而不会杀死存在癌症的人。或者你知道,上帝帮助你,试着让婴儿更聪明。
在相对短期内发现最令人兴奋和最合理的最令人乐趣的事情正在致力于致命理解遗传疾病 - 能够修复我知道我的伴侣和我俩对遗传疾病的倾向相同的遗传疾病,但如果我们具有这种基因的功能副本,我们会很好。因此,如果我们可以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机制可以在体外修饰胚胎,这是在开始之前治愈疾病的潜在令人兴奋的方法。有些人我关心的是,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交易。
一些疾病,你可以通过有一个有限数量的细胞来治愈,这是正确的,即使它们被做错的细胞包围。例如,如果您因任何数量的疾病导致生产白细胞的能力,而且我能够修复一些骨髓,或者我可以在胰腺内给你产生胰岛素的基因否则完全失效,那么我可能能够让你的生活更好。
我认为媒体炒作来自这个想法,我们现在可以在成为人类之前对单个细胞进行修改,很快 - 或者已经已经 - 我们可以修改细胞或将预修改的细胞推向现有的人类。这有可能修复以前无法使用的问题。
但这仍然是真的,真的很难做到,而且它相对于真正的裁缝可以做的实际范围并不是很聪明。在基本的科学应用程序中,像我作为我博士学位的一部分开发的应用程序,使用该系统更多地区兴奋更加接受在实验室中之前不可能的结果。它不仅仅让科学更容易;它使它非常容易,这现在是全新的事情。
为大型软件公司工作,在学术界工作在工作条件下具有非常不同的声誉,并且通常如何完成工作。你在那种过渡时遇到了一些文化休克吗?
软件公司和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的特定计划是一个奇怪的家庭丢失玩具,只要他们实际上试图通过培训招聘那些不是生物学家的人。所以我没有觉得在外面凭借我预期的生物学背景。
就实际学科而言不同,工程与科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而人们谈论问题的方式。 这是十字架最难的桥梁。 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当面对问题时,我会努力绑定这个问题。 我的思想过程是:好的,有这个问题空间我们正在努力工作,所以让我们弄清楚最好的案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