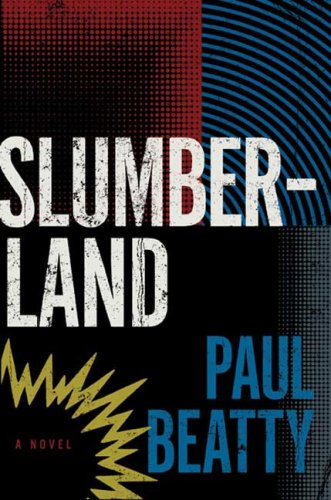我们的事:采访保罗(2015)
Warning: Can only detect less than 5000 characters
他首先在七十年代写了那篇文章,尽管他正在修改它。这家伙的研究是关于,因为缺乏一个更好的学期,一个自我实现的黑人是或者更具体地是一个黑人的男人,而不是明确的,它只是读得很男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他多年来更新,它进化了。与性别相比,它变得越来越少,而且与民族主义的黑色意识联系在一起。它变得更加接受其他思维方式,其他方式看世界。这真的很有趣,作为黑暗的宗教信仰,在比赛中,改变了他对这种普遍种族身份的想法改变了,而且在他调整后,这篇文章也变得奇怪地对比赛变得奇怪。考虑他所做的进展真的很有趣。它可能像黑人作家所描绘的方式和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样平行。
你认为白色作家以黑色作家的方式写下比赛吗?
我认为他们这样做。也许没有明确。我正在努力想到一本书 - 但几乎任何事情都会做,真的 - 现在通过白色作家写的最佳卖家列表中的任何一件事。它与黑暗或海洋或拉丁美洲或其他任何东西无关。我认为这对比赛的评论是别的什么,是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问题是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只是认为他们写了关于共同经历的写作,我们认为这只是世界的方式。
他们不必是。没关系。我意识到它。我可能错了。但这是我很久以前学到的一课,在M.F.A ..学校事实上。 Ginsberg缺乏一次,Gregory Corso进来了。我们读了我们的诗 - 这是我和这个诗人名叫凯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另一个诗人,帕梅拉休斯。我们三个人读了我们的东西,Corso很生气,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处理我们在做什么。因为它不是狗屎,他关心。他一直在说,你的普遍性在哪里?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以前大声争辩。我就像哦,这位母亲认为他是看世界的唯一途径。我意识到这与任何东西都是如此。我有一个可怕的习惯,可以在我的车里听到体育收音机。并再次,他们谈论的80%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比赛 - 他们谈论的是,他们如何谈论它,他们谈论的是,他们在谈论某些球员时使用的语言,他们不喜欢的话使用。这是关于种族,这是白色的。他们不知道它,很容易争辩说不是。但它是。
他很生气。我们也很生气。但是,学习是一件好事,关于人们如何看待事物的区别,为什么人们看到某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映射过这件事或写一篇关于它的论文 - 但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它类似于人们如何看到情节。我认为情节是非常主观的。如果一本书关于你关心的东西,那么它并不重要;作为一个读者,你以一种感觉像图标的方式被捆绑在一起,感觉像结构一样。但如果这本书是关于真正的事情,真的,真的与你的读取方式相切,或者在你的世界中的东西,你的反应可能是哦,这里没有情节。
但是,另一种看着它的方式。我记得有一天碰到格雷格·泰特特,我们正在谈论某些东西,只是蜿蜒到处都是蜿蜒的,他说,好吧,你知道黑鬼无论如何都无法留在这个问题上。而且我就像,哦,现在这是一个整体文化的东西。我不一定同意这一点。但对于他而言,也许,这是我们的方式。
我一直都在你的工作中喜欢这个句子,也是句子的积累 - 你经历了这些进攻,觉得他们非常受控,就像笑话的建造一样。你做了很多修订来实现这种影响吗?
每时每刻。从词到单词。这都是他妈的修改。我总是回去。我会首先写作,但是很多页面都感觉到,比如五页。然后我回到那些五页的顶端,然后向下写下我的方式。直到我对那个街区真的很满意,我不前进。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在那之后,我再次回到整个块,只是为了确保它更紧,更紧。所以最终我必须或多或少地是整个事情的初稿,这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我只是想到了很长时间,并且没有在页面上做任何工作六个月,这是我与我的编辑的Colin Dickerman相遇,他有一些好事来建议。在那一点上,它足够紧,我可以回到并撕裂它并改善它而不会丢失任何东西。我可以拿出大屁股块,仍然想到自己,是的,它仍然在工作。有一些明显的事情,我会说。
我知道他要说,你需要更多这些耳语潜在的剧集,就像读者看到他这样做的更多机会。 [在卖出时,黑鬼窃窃私语是叙述者心理学家父亲开发的一种简易谈话治疗,“每当一些黑鬼丢失的人失去了他们的母亲忘记”需要从树木或高速公路立交桥悬崖上谈论。 “]我知道他会说,你需要更多的父亲。我认为自己,这不是关于孩子和他父亲的一本书。我为响应科林的产品而做的一件事是增加了射击和埋葬和背景的更多东西。科林还告诉我,将所有书籍的行动搬到狄更斯的范围内,这确实有助于将行动集中起来。我确实尝试做更多的小孤立的黑鬼潜在的剧集,但它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不知道。他可能做了,但我不能这么说。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读了Heller和Vonnegut,你说他们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力。像vonnegut这样的人我一直认为是一种讽刺性的人,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 有一些肯定的东西,但有些东西对vonnegut来说也是恶毒的。然后有切斯特·他,我所爱的是,因为他确认了我相信的东西,这是真正重要的,只是孤立的荒谬层,堆积起来。你觉得你一直在写这个传统吗?
我想你很容易把我放在那里。我不是在尝试。但是你可以把我放在那条车道上,我不会抱怨这么多。
一点都不。在我的脑海里,它会限制我能做的事情,我如何写一些事情。我只是在写作。有些人很有趣。我很惊讶,每个人都会呼吁这部漫画小说。我的意思是,我得到它。但这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不要谈论其他任何事情。如果他们以连字的方式谈论它,我会更好地了解它,甚至是悲剧性的小说。书中有喜剧,但还有一堆其他东西。只需隐藏幽默就很容易,然后你不必谈论其他任何事情。但我绝对不会将自己视为讽刺家。我的意思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记得纽约人封面每个人都说的是讽刺吗?巴拉克和米歇尔拳头撞击?这对我来说并不讽刺。这只是一个评论。只是嘲笑某人的乐趣并没有讽刺。这是每个人都在很多抛出的一句话。我不确定我如何定义它。
你用一些读者写一下吗?您是否觉得您正在为您的读者提供关于某些事情的想法,颠覆或上层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
我想我是。我写的时候我不会想到它。我正在和朋友谈话,她说,你的观众只是一群怪异。但她以非常积极的方式意味着它。有一种特殊的怪人会欣赏它。至少,我认为这就是她所说的。
我一直都觉得 - 这是我自己的自恋 - 我实际上是你的目标受众。但我不觉得浮夸。
因为你是黑人,你所在的年龄,你旅行的世界,你旅行的圈子。有人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这很长一段时间。我正在读一首诗,这个女人说,这一定很难成为你。而且我就像,为什么,你在说什么?她说,因为每个人,无论他们是谁,他们只能得到一半的笑话。而且我就像,哦不,不要这么说!那只是搞砸了我。但我完全理解了她所说的话,然后我只是不得不放手。
在纽约时报最近的托尼莫里森概况中,莫里森评论说,她对没有“白光”的写作感兴趣,没有任何外部压力,关于她的书应该是什么或者它们应该如何感受。你曾经对你的写作感到任何压力吗?例如,您是否曾感受到您需要对您的小说有更熟悉的结构?
不不不。这几乎就像黑色的情趣族人会有一个完全无用的白人角色,或者一个白色的情趣族将有一个完全无用的黑色角色,将观众置于某种东西,以确保在那个奇怪的全景中,观众就像,哦,这是我适应的地方。我不认为我完全这样做了。我甚至没有谈论它。我一直在拥有关于当代书籍的所有这些对话,并且如此奇怪的是,这些书籍为某个目标受众 - 主要是白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他们的反应非常响应。但这本书是为他们写的!这绝对没问题。没有人谈论这一点。这就像,哦,好的,那很好。这些书籍得到了某种关注。我会看到它并思考,感觉就像潘宁一样 - 但这只是这些人想跟谁说,这绝对没问题。我希望我不是这样做。我不认为我这样做。
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意识地认为我不想要那个白色凝视,虽然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希望在我的怪异的观众中,有一些所有种族的人。随着人们的颜色,作为黑人,我们都必须有这种能力来讲这些不同的语言并制作这些不同的参考 - 我们不必拥有它,但它有帮助。所以对我来说,它仍然是一件大事,这些文化重叠比他们拥有的更多。你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希望这个“真正的愤怒”的东西仍然针对他们,而是一种奇怪的我想要狭缝你的喉头方式。我不是说那些人不是观众的一部分。我只是大喊大叫。我知道他们的耳朵会听到。但我希望那里有一吨耳朵听到。即使我无法真正帮助,但我努力不要在一个方向上大喊大叫。
我们之前已经谈过了关于一些作家如何不去一个冒险的地方。当你写作时,你会把自己放在哪里,你觉得某种恐惧或真正的风险吗?
是的,我试着一点点。其中一部分恐惧只是批评我真的很喜欢的狗屎,即当我批评民权运动时,我真的尊重一些水平。不批评,但戏弄并解析出它的某些方面。我的意思是,你如何涉及民权运动?所以有风险。有风险的风险是关于我自己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的,但同时我必须尝试这样做。有时幽默是一种掩盖所有的方式,所以读者不知道我写的是我的是我,或者弄清楚我的争论的一面。然后只是试图说出你的意思。而不是,正如我们所谈论的那样,不要对我所知道的这个目标群体发言,如果我想,我可以取决一定程度,并告诉他们他们想要听到的狗屎。我想如果我想,我可以这样做,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这样做。我了解到我不能这样做。无论如何,写作是一种风险。我不认为有风险,我会让自己疯狂 - 我不会做一个Sylvia Plath。但这是我写的很多的秘密文本。例如,我的工作中有很多自杀。这些是以真正的方式对我个人的东西。
你确实谈论了你的工作死亡和损失 - 以及漫画小说,对卖出的强大挽歌质量。总有某种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短暂地在你角色的心中形成。某种英勇的使命或乌托普的可能性消失,刚刚脱离了。有时我觉得幽默是一种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损失和失败。即使是没有任何改变的想法是我们谈论那种存在荒谬的建议。
我觉得我最近看到了一些纪录片,他们在那里谈论这一点。人们如何应对失败。你从来没有关于如何处理这个狗屎的课程。我记得在大学里,我的朋友们正在谈论旧的勤劳的追踪,你知道你努力工作,你的梦想会成真。我的朋友说,我爸爸是纳什维尔的一个门户,他的整个他妈的生活努力,他的梦想都没有成真。我想要的是只是为了写作。努力工作进入所有这些。但没有保证。我做的很多幸运就会变成年龄。写作是一种我可以回去的方式,想想之前的东西。就像在书中我有马丁路德王说,男人,如果只有我尝到了他妈的冰茶在那些被隔离的午餐柜台上有多讨厌,我从来没有开始这件事。它回到了这个问题 - 这是值得吗?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值得的 - 我的意思是,显然它有 - 但我们不知道如何衡量它。而且我们无法衡量它的那种内疚,我们有一些幸存者的内疚。
同样的问题和问题继续表现出来。我记得读一些射击者在叙述者基本上说那个是那么受欢迎的另一个剧本 - 这是一件好评的狗屎,这只是毫无价值的商业东西。所以即使这个想法也是老 - 我是真的,他们不是真的。这让我翻了出来,但这也很舒缓。所有这一切焦虑,所有这些都是觉得,就是制作艺术。这太古了。我们拥有的讨论,人们已经长时间拥有了它们。不是工作没有改变 - 当然它有 - 但这些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仍然只是人类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