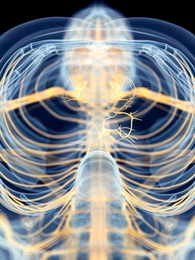放手:我的战斗帮助我的父母死亡
一旦Covid被创造出来,我的父母就会更新他们的“前进决定”文件。他们不断调整他们,微调他们对未来的医疗的愿望。 “就像一个令人作造的骗子一样,”我戏弄他们,吹掉墨水在另一个签名上。
20年前他们首次完成其提前决定文件的时候,他们大多关注没有被复苏,如果他们在市场上购物或骑自行车的时候。现在,年龄在84岁和82岁,并被多种疾病衰弱,他们必须放弃他们的自行车和那些希望戏剧性的人。 “我们看起来像老人的道路标志,”我的妈妈说,在她的拐杖上弯曲,递给爸爸他的棍子。他们这样做。脆弱作为叶子,他们蹒跚地走到素食咖啡馆的道路上:风可以把它们吹走。
这些天,他们真正想要的只是避免医院。他们希望在家死去。为此,我们已经买了一张医院床,楼梯升降机并改编浴室。但是,在Covid-19面前的使用是什么,他们担心:疾病,他们读(因为没有什么是巩膜的内容,他们的摄入新闻),这不仅仅是对他们来说将所有人留在风险?如果他们有Covid,谁会护理他们?
“好吧,我,”我说。 “我会做的。我只是围着拐角处。而且,看,我已经突破了法律,只是坐在这里。“ (对于4月份,4月2020年,支持泡沫尚未发明。)“我不害怕,”我撒谎。 “写它。”所以我的父母写了他们的Covid Codicils:没有医院,没有通风。请止痛药。
也许他们不是那么异常。事实证明,有一个政府驱动器让GPS与弱势患者交谈,避免在Covid面前的英勇干预措施。这个驱动器经常似乎导致对当地广播电台的愤怒呼叫,但我的父母在GP戒指时感到高兴。不久之后,他们拨打另一个政府赞助的,提前决定文件填写。这一个是绿色和一点基本,但它带有一个特殊的锅,将其放在冰箱里和救护车的承诺将永远看起来。我的父亲对这种细节很满意,他将所有以前的预先决定的文件夹夹在冰箱门上,所以护理人员也会找到它们。 Covid-19这个文件夹说,在这样的哥特式摇摇欲坠的首都,经过一段时间的母亲无法看到它,并用纳迪亚的报纸剪辑覆盖它,据报道,据报道,有科迪德。 “纳迪亚变得更好,”她说,看着老虎亲爱的镶边脸。我的母亲喜欢猫。我的母亲喜欢很多东西:烹饪,收音机,所有的孩子,鲜花,我的父亲。她不懈地希望,坚持像春天。
但是这个春天,我有时会认为我的母亲正在死。当她站在盛开的黑色植物中时,这想到了我,当她要求我在肉汁中品尝盐时,因为这种感觉已经消失了,当她痛苦,突然时,记忆只有我会注意到,我会注意到请乞求我忽略它们。我的母亲已经承担了多年的衰弱的疾病,总是把她的头抬起来,明亮和勇敢,总是在街上出去,发现她的慰借与人交谈。但是当我在这些早期的检疫早期说服她时,家庭确实详细说明了我们周围的避免,把他们的小孩拉开了。有一天,一个疯狂的人吐在她的外套上。另一天,邻居用消毒剂喷洒她,并让她想起她的购物。我母亲的脑袋倒了。她说我们应该得到这个,因为当我和他们出去时我们正在违反规则。她不会再来草地。
当我的母亲在晚上是一个兴奋的孩子时,一个跳跃的杰克烟花厉害地烧了她的腿。现在,随着她的心脏旗帜和她的腿膨胀和她的皮肤,从数十年的类固醇,裂缝削弱;溃疡和蜂窝织炎出现在古老的疤痕中。我用碘垫打孔,用蜂蜜擦干,拍摄新溃疡的照片,因为它们出现并将其发送给医生,通过从化学家返回来接受抗生素,购买imodium和益生菌来处理苛刻的副作用。
我父亲的父亲担心他的新帕金森的诊断,他的颈部肌肌肌肌肌肌,迫使他的下巴,他的癌症,再次复活,总是,他的抑郁症。每天我们都走在草地上的同一个环,每天都能找到更长的时间。他的谈论比习惯于过去:他的学校,兄弟姐妹和堂兄,他年轻时失去了。他谈论 - 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 关于他自己的父亲,亨利,缺席海军情报任务为他的大部分童年。他检查我知道在哪里,经常会在哪里,并使我承诺立即去除纳迪亚虎的照片,如果他或妈妈会生病,那么文件会更容易找到。
令人惊讶的是,纳迪亚一直在11月下旬到11月下旬的早晨,当我的母亲身上有另一种感染,醒来寒冷,无法移动。我们称之为守护救护车的医生,这太迅速地带来了,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打包她的行李,把她的提前决定放在一个特殊文件夹上,在收音机顶部和帕特里克大风小说上,几乎没有时间把她包成她的好东西梳妆台,梳理她的头发,告诉她,她看起来很漂亮,即使是现在,因为她有优秀的骨头,在救护车把她带走之前。
M y母亲因健全的原因而害怕医院。像医院一样,这一个是善于英雄的干预,不太擅长护理。它是一个具有许多突破性的研究人员的学术机构,但脆弱的老年人有乏味,多种条件对他们来说不是兴趣。当我的母亲紧急胃流血时,她很干净,但当她脊椎疼痛时,她留下了一只小车的四个晚上,甚至在一个点上剧院,让别人的操作(幸运的是她被转身回到门口)。
Covid限制已经加倍这种趋势。这一次,她用Hoo-Ha和激烈的抗生素治疗了疑似骨感染,然后用多个药片来制作赛车的心脏,但是当扫描揭示感染时不在那里,她在一个病房里留下了一段时间在没有结论性诊断的情况下被释放。通过所有这一切,因为科维德,她必须独自一人。
当她回到家时,许多事情已经失踪了:提前决定文件,她的消化,她能够到达厕所,她稳定的心跳,她的信心,她记忆大的大位。例如,她忘记了我的父亲有帕金森的。她认为他可以把她的托盘带到楼梯上,他陷入困境,他的头上挂在胸前,手摇晃着,陷入了他的萧条,思考我的母亲躺在床上,明亮的眼睛和愤怒,朝外她对精心制作的午餐计划的恐惧。我来拿走托盘,他说他想死。
我的父亲认为他的死是池塘的船。 “你只是出去玩了一个美好的时光,”当他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的时候告诉我,“拖着桨,他们在你的号码中呼叫。进来,63号。可能很快,也许,但这没关系。“那很快就是:但是,这是12年前,癌症原来是可容纳的。它回来了,但我的父亲现在都不相信它会杀了他,也不会太快就会杀了他。他害怕什么都不能杀死他。 “医生总会想到一些事情,”他说。 “他们会继续抽你的,让你活着。”
在一个竞标捍卫本医院,努力了解我母亲的提前决定文件可能已经消失的地方,如果它重要的话,在写死亡的最后一次射门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清楚信(总是我的父母的父母武器选择)我们要求GP来实现终身会议。非常友善,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大流行的第二波,她参加了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听。她也担心提前决定文件的命运。他们必须在紧急情况下丢失,可能在医院访问时早期,因为排放笔记有我的母亲“用于复苏”。 GP说她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们拿出了原始文件 - 仍有很多副本 - 并尝试下次计划。我听说有社区护士如果你正在垂死,那么将给你吗啡的护士,让你滴水,但GP不会确认这一点。 GP有一些替代方案:一位老年人,一个社区医院,但你仍然要叫救护车。
它不需要很长时间。在圣诞节之后,我们必须在妈妈的腿上致电GP关于一个新的溃疡。护理人员来看看并提出担忧。他希望在医院的一天病房中测量母亲的心率。当天的病房,他承诺,而不是紧急单位,但她进入11次,又来下了下午4点,所以我打电话给病房,我告诉她从未到达。我打电话给交换机:她被转移到了紧急单位。所以我打电话,它响起了钩子。我再次召唤号码,然后再次调用。我每两分钟给它一次,直到晚上10点,只有一次被拿起。护士告诉我她太忙了让我与任何人交谈,有一个流行病,但她可以看到我的母亲穿过病房,活着和抗生素滴水。我去睡觉。
早上3:30,我在手机上醒来。他说,我的母亲在溃疡中开发了败血症和疾病感染。他们会运作,她可能会死。我很困惑,我说她已经提出了对这种情况的干预措施的医学决策。哦,好吧,医生说,我们正在和她合作,她很满意。她非常明亮,非常警惕。他把电话放下了。我想象我的母亲,温顺和微笑,因为她总是在恐惧。我记得她如何同意去运作并不是她的操作,沿着走廊滚动,明亮和微笑着医生。我想象她的感染腿。我想她醒来发现它消失了。我想到了我不够快速地向医院送到医院是所有的错。我起床,然后去看我父亲。那天早上有沉闷的雾,好像我正在吃它,好像我的内部是充满了雾。
我的父亲和我再次出去了预付决定。他们太清楚了。 “如果发生感染我想要避免英勇的干预”,“我用呼吸机拒绝治疗”,“如果替代方案是永久护理的话,我不希望我的生命长。但她没有和她有那些文件,因为她要去天道。她为我完成了完整的医疗律师文件,但由于Covid,我不能在那里倡导她。现在她已经被戴上了呼吸机,因为她的手术,当我称之为ICU时,他们说她陷入困境,她无法呼吸自己。他们不知道她是否会脱离它,但如果她这样做,他们说,她会在养老院生活中的一个非常有限的生活。 “我们必须希望她死了,”当我放下电话时,我爸爸说。我的父母是虔诚的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没有上帝,因此我们必须活得很好。所以我祈祷。
然后我开始扫描我母亲的文件并将它们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ICU。在2021年1月,这似乎是一个特别难以做到的事情:当整个国家都被吸收努力拯救像父母这样的人的生活,当国家精神科剧重点是让老人进入呼吸机时,没有脱离它。我担心医生会认为我是一个凶手。
但很多医生都相信一个很好的死亡,其实希望迫切需要向患者提供。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感谢提前决定。母亲在ICU的母亲照顾的医生当然是其中之一。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对母亲稳步失败的肾脏和稳步持有和平死亡的长期交谈。她向我保证,她会不会更多的英雄干预措施,我们将被允许终身访问。两天后,她把母亲从呼吸机上移开,所以她可以舒服地死去。我的父亲和我被召唤到ICU吩咐她的告别。我的母亲在宁静的病房里躺在一张高床上,通过她的面具嘀咕着“爱的爱”。这是难以忍受的动作,只是略微戏剧,只有一件事出错了:她不会死。
24小时后,我是我哥哥的那个兄弟。他在黎明中遭到了残疾的隔离和驱动的距离,并恳求并恳求自己,父亲依赖他的想法是姑息的病房,只有一个氧气面具,有意识,而是从她的头上找到呼吸。一位医生问我的兄弟是什么样的“房子周围的清洁帮助”是“当她回到家”时的可用。我哥哥是,可以理解,全部全部创伤。
他只希望,我们锻炼身体,让我的母亲从医院出来,她再次看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就是将她和我的父亲搬进私人护理家,在那里他们可以分享一个隔离房间。我父亲愿意。医院说有可能。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做到的养老院。现在我们必须告诉她。这很难:医院处于完全大流行模式,我们每天都致电信息,小心翼翼地定时捕捉护士。我的兄弟和我在rota - 如果我们都在24小时内尝试致电,我们将被告知。
我注意到我的一个感情,因为我求知道我的母亲仍然活着,是羞辱,另一个是愤怒,但主导是一个无助的,这是极端的,它导致我带来了冷漠。这些感受的版本,我含糊地假设,是跨越全国革命运动的原因,去除老年人免于孤立在护理家园里,而且为什么我父亲已经停止进食,似乎无法品尝任何东西和花费他的大部分时间看着墙。
在第五天,我被医院打电话。这是一个新的高级护士,询问提前决定文件。似乎我的母亲一直把饲养管拉出她的喉咙,宣布她有一个。坚持不懈。这位护士认为这应该听取。她是如此明亮,我的妈妈。她抬起头来。我喜欢这位护士。我再次送下文件,护士发出新的安排:我的母亲是被允许为自己吃饭和喝酒,无论窒息的风险如何。
现在管道出来,她可以说话和持有电话。我被允许和她说话,我不知所措,发现她仍然存在,我心爱的母亲,仍然存在强烈的声音,渴望,异常肯定。我告诉她关于我们的护理家庭计划:我们将会让她出去。很快,她将和父亲在一个房间里。她哭了。 “我从未想过我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她说。 “我以为我已经死了。我以为你们都死了。“
但当她当然不允许,真的。两天后,她测试了Covid-19的肯定。她没有特别的症状,但她必须留在医院。之后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也测试了积极的。大多数人可能会在与兄弟的第二次访问第二次访问。 Covid是为什么他不能品尝任何东西,都不能说话或搬家,事实证明我已经足够强大,以便毕竟护理他。我遵循所有指示来隔离,送走我的孩子和所有的帮助。我父亲和我坐着看墙壁。
我不能让自己告诉我的母亲护理家庭计划已经崩溃了。在我和她一起的另一个电话里,我说她已经出去了,她说我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冠军。我很快就说她会回到前室里的大椅子上,我们将成为橘子酱,是季节,她说这就是她想要的。然后她说晚安。当医生手机在第二天告诉我她已经死亡时,我并不令人惊讶。
首先,我的父亲不接受它。三天,他大多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完全全神贯注于对他的身体担心:如果他需要厕所,如果他都会陷入困境太冷或太热了。然后他的孙子们来绕着窗外站在窗外,他突然充满了喜悦。 “我以为我已经死了,”他说,就像母亲所做的那样。 “我从未想过这么一天会来。”
但是,通过这种觉醒来实现我的母亲真的死了,他必须没有她。他无法想到一个良好的计划:他们彼此生活的程度完全暴露。他解释了我已经注意到的东西:他的帕金森的意思是他不能再键入,并正在妨碍他的阅读方式。没有更多的学术文章,任何帮助年轻人都有他们的博士。他的书现在都写得。
“好吧,”我说,“他们是好书。”当他躺下睡觉时,他说:“我想到了,你知道,每晚都知道。我要这样做。“
在夜晚,他的船被召唤。在早上,我发现他瘫倒在床上,呼吸嘶哑,大多是无意识的。我拿出了提前决定,他和我的母亲,并通过了全部阅读。我打电话给医生,说我的父亲有一个中风或心脏病发作,请问我可以和某人说话。
“我不会那样做,”我说。 “他对此做出了预先做出决定,很明显。”
“你必须拨打999冲程,”接待员说。 “去年我的丈夫有一个中风,这就是我要做的,如果你不叫999,你就不能有任何帮助。”
“好的,”我说,“我们不会有任何帮助。请你通知医生?“
这结果是正确的话。最后,绝望,拒绝,我的父亲和我通过看起来的玻璃,进入家里奄奄一息的世界。我们很惊讶地感谢,即使在2021年1月,GP也会来到房子,区护士每天都会致电两次,并用司机司机为吗啡和一个梦幻般的新抗焦虑药,第一个,也许是触摸他的问题。 “我这么印象深刻,让我生意,”他对护士说,在最后一次他完全睁开眼睛之一。
“自己,”所有这些游客对我说,虽然不清楚我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理事会告诉我,我有权获得护理人员,但由于没有任何照顾者,我不会得到任何。但是,当它得到太艰苦时,我的兄弟出现,我的堂兄,我的侄女和侄子,我的孩子,我们管理。我的父亲会听取消息并向我们说再见,然后挣扎,然后睡觉,然后,10天后,死亡。死亡的主要原因是Takotsubo心肌病或伤心的认证。 Covid-19,因为它是我母亲,被列为次要原因。
因此,我的父母都成为关于这个消息的统计数据。他们是如此多的方式典型的covid受害者 - 究竟是一个与许多共同的中位年龄 - 我觉得我应该能够在这些数字中找到它们,当国家默默地沉默并为此造出旗帜而哀悼他们堕落。但是很难。我的父母没有争夺那场战争。如果Covid缩短了自己的生活,那就不是很多:锁定的孤独袭击了他们更加困难。他们不想打击死亡:他们试图让它进去,找到一种人的方式。这是一个非凡的,揭示了在大流行中间的NHS的价值观,他们的医院毫不犹豫地给予高科技应急操作,并在呼吸机上给某人带到我母亲的人身上,但也表明了我们在死亡周围的规范,没有人停止询问她是否有提前决定。
但是我们的家人并不是他们的死亡“撕裂”,因为目前的叙述要么是它 - 肯定不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