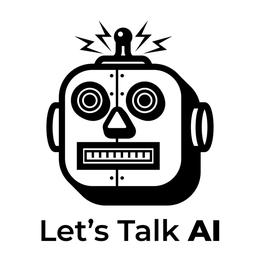Acheiropoieta:关于不是用手制作的艺术品
如果一个人倾向于在广阔的eBay宇宙中搜寻老式的流行杂志,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悖论:1949年8月1日,《生命》的封面印有Joe DiMaggio的价格不到十五美元。仅仅一周后的8月8日,封面上有一位风度翩翩但名不见经传的女士的照片,其报价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二十倍。稀有性当然不是原因;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是。在那期令人难忘的四页画中,这位画家立即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那个魁梧而蓬勃的男子怎么办?在一个谷仓里跳来跳去,疯狂地将油漆从罐头倒到铺在地板上的画布上?闻所未闻!可以认真对待这种st头,还是这些假冒艺术界巫师所犯下的另一个骗局?传说1946年,一幅Pollock帆布从美国艺术家财团到达佛罗伦萨,为Bartolomeo Ammannati 1569年的杰作SantaTrìnita桥的重建做出了贡献。这座城市的父亲认为这笔礼物是一个残酷的玩笑,并迅速将画布托付到了垃圾箱,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怀抱中也许并不完全令人惊讶。如果这个故事不是伪造的,那很可能是1975年Thaw / O’Connor目录中没有列出的唯一的波洛克。
实际上,波洛克并没有被忽视。在生命故事发生很久之前,这位艺术家就获得了颇有影响力的画廊主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的支持,他与他于1943年签署了一项协议。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于1956年12月举行了一场全面装扮的回顾展,距离艺术家过世的死亡仅四个月。如果一开始没有被伟大的未洗者所接受,那么波洛克已经在美国战后艺术万神殿的上游稳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个人生活的动荡和四十四岁时的戏剧性死亡促成了神话。
波尔洛克的作品引起了许多反思,但与本篇演讲主题特别相关的是他的绘画方式-将图像作为身体行为进行制作。观察到此行为后,立即显而易见的是,艺术家的手与画布上的结果脱离了距离,即颜色到达绘画表面之前必须经过的距离。这种超然脱颖而出在创造过程中注入了一个关键且完全前所未有的元素:纯粹的机会。尽管对波洛克的创作中最重要和最具创新性的作品“滴水”的绘画经常受到人们的钦佩,但他的技术内在的巨大变量却无法得到充分强调。在他之前,没有哪个艺术家对如此简单的运气大为放弃。可以说,波洛克将手与画布分开的距离“擦除”了他的存在。
尽管乍看之下不尽相同,但Pollock的过程与传奇的完美主义者Jeff Koons使用复杂的计算机程序确定雕塑或绘画的每一个最细微细节的方式奇怪地平行。这位艺术家耐心地坐在他的Apple控制台上“创作”,而最终的真正作品却出自训练有素的工作室助手的手,几乎不受作者的触动。起初,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机器,在人工制造中篡改了人工干预。到20世纪中叶,机器人-极为灵巧的机械“手臂”和“手”已经成为流水线固定装置。整个过程由计算机技术控制。
波洛克和昆斯虽然有明显不同的方式,但我们正回到一种“无手制造”的艺术的门槛上,这种现象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白手起家”。它是中世纪的希腊语单词,定义了无需人为干预即可出现的几种图像或符号类别。被视为奇迹般的事件,在不同的时间都受到崇敬。旧约圣经(但以理书5章)中引用了一个早期的例子,当时,在奉献国王伯沙撒的盛大宴会上,宫殿的墙壁突然出现了不祥的警告。铭文是用一只不熟练的手“写”的,这是一种非人类的表现,使组装的公司感到震惊。在此类超凡脱俗的事件中,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是“维罗妮卡的面纱”,它代表了中世纪早期的无数版本。女圣人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她跟随基督在去v髅地的路上,用一块布来擦洗他那鲜血沾满汗水的脸,从而奇迹般地给他安慰。这个故事没有出现在规范的福音书中,而是由被称为“彼拉多的行为”的伪经文本组成的。这位圣徒的名字曾被称为“维拉”和“伊康”(真实形象)的虚构结构,在意大利也被称为“伏尔托·桑托”(圣洁的面孔),被尊为基督的“肖像”。
可能最著名和最具争议的疼痛症是所谓的“都灵裹尸布”。亚麻纤维织物的长度为15乘4英尺,以人字形编织而成,带有淡淡但可识别的裸体男人双重形象。幽灵般的身影被看作是基督在葬礼上的形象的视觉见证。首先提到的是1354年法国令人费解的文物,此后它最终被萨沃伊公爵所有。圣布是否丰富了都灵及其统治王朝的精神生活尚不确定。它无疑对欧洲巴洛克式建筑的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在1688年,萨伏依公爵查尔斯·伊曼纽尔二世委托著名建筑师瓜里诺·瓜里尼(Guarino Guarini)为珍贵的圣蒂西马·辛达内(Most Holy Shroud)建造了合适的避难所。结果是无与伦比的杰作,仍因建筑物几何形状的复杂性,巧妙的开窗和材料的创新使用而广受赞誉。它直接与都灵的皇宫相连,直到最近,它仍然由萨沃伊家族管辖。
“维罗妮卡的面纱”并不是那么幸运。如果它曾经存在,它就不会幸免。最早的记载是1129年,两名朝圣者从圣地返回意大利,此遗物可能在1527年的罗马大袋战争中失踪。深色的,斑点状的,不确定的材料和年代保存在精心制作但困难的地方去看圣彼得的圣地。它几乎不算在大教堂的主要景点中,通常位于教堂中殿右侧的三叉戟中。相比之下,维罗妮卡(Veronica)的伪经故事在教堂礼拜仪式中占据着永久的地位,是第六个“十字架的驿站”。世界各地每天都有无数次被引用。虔诚的维罗妮卡(Veronica)在视觉艺术领域也保持着主导地位。她的面纱及所有作品都出现在范德·韦登受难三联画的右边,现在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在意大利和北文艺复兴时期,对圣徒的这种肖像画一直保持不变,直到十七世纪才让其进行更自由的解释。在圣彼得大教堂中,维罗妮卡(Veronica)出现在雄伟穹顶下方的中殿和透明壁交叉处的四个巨大雕像之一中。它是由弗朗切斯科·摩奇(Francesco Mochi)(1580–1654)在1629年执行的,四肢,被风罩和头发蓬勃发展。这位法官的工作还标志着巴洛克风格的权威性,这是一种视觉成语,以戏剧性,动感戏剧性和技术巫术为特色。
妮可·布莱克伍德(Nicole Blackwood)的一篇学术文章在意大利版画家乌戈达·卡尔皮(Ugo da Carpi)的作品中(约1460年至1525年)检查了面纱的显着幻影。虽然这位画家的图形作品在意大利和国外广为流传,但据悉他只执行过一幅画:一个大面板,代表圣维罗尼卡举着面纱的中央人物,旁边是圣彼得和保罗。从布莱克伍德的文章中的照片来看,乌戈很可能坚持他的图形追求。面板上展示了稀缺的艺术礼物,更不用说绘画了。尽管如此,它似乎是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调试的,尽管目前似乎没有展出。布莱克伍德指出,她的文章“一方面说明了奇迹般的绘画创作理论与另一方面的艺术创新与作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她的选择特别合适,因为它代表着女性的圣女手持大面纱,上面带有明显来自圣彼得遗物的“ Volto Santo”图像以及它启发的众多已知复制品。 Ugo绘画的有趣之处在于签名:“ Per Ugo / da Carpi Intaiatore / fata senza / penello”(“无刷Ugo da Carpi木刻雕刻机”)。布莱克伍德(Blackwood)对祭坛的仔细检查揭示了乌戈(Ugo)铭文的真相:存在大量的指纹和“手指抚摸”,可能是画家自己的。瓦萨里(Vasari)的创作稍晚一些,他几乎一如既往地了解情况,这证实了乌戈(Ugo)在其艺术家的“生活”中的独特技巧。
寻找其他的acheiropoieta可能会鼓励一个顽强的旅行者去寻找意大利东南部很少参观的阿布鲁佐省的马诺佩洛村。那里是城镇郊区的一座漂亮的避难所教堂,建于17世纪初期,但在上次战争的惨烈破坏后得以修复。它在其主祭坛上展示了一个简单的银色圣物箱,上面刻着一个男人留着胡须的脸的模糊图像,上面涂有丝绸。德国耶稣会士学者海因里希·菲佛(Heinrich Pfeiffer)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将“曼诺佩洛图像”(Mannoppello Image)推广为“维拉·伊康(Vera Ikon)”,尽管该人的特征具有很高的绘画品质,并且与后期的绘画风格相似Trecento意大利艺术。具有艺术感的历史学家罗伯托·隆吉(Roberto Longhi)和费德里科·泽里(Federico Zeri)可以轻松地将图像归因于特定艺术家的手,这与“无手绘画”相矛盾。
追溯到中世纪的棘手的神秘领域与当代艺术有关,其中一些是“没有人手创造的”,至少一部分是在波洛克和昆斯的见证下进行的。但是接下来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步:从概念到执行,完全由机器创造的艺术品。这样,一个理性,有文化的人就会踢入并尖叫到当代的“人工智能”(简称AI)的反乌托邦中。该学科的公认先驱是爱德华·费根鲍姆(Edward A. Feigenbaum)教授,他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毫不奇怪,人工智能软件的概念浮出水面在加州学术界。费根鲍姆(Feigenbaum)1963年出版的《计算机与思想》(Computers and Thought)是该学科最早的治疗方法之一。自然,艺术没有出现在讨论中,也没有出现在费根鲍姆(Feigenbaum)于1977年提交给斯坦福大学的“启发式编程项目”中,但标题是:“人工智能的艺术”。该文章摘要的开篇词应该在每个有思想的人的心中都感到震惊:“知识工程师实践把AI的原理和工具用于需要专家知识来解决的棘手应用问题的艺术。”这不让人想起狗咬狗的尾巴吗?
踏入这个勇敢的新世界,寻找“知识工程师”和AI艺术,人们在网站上偶然发现似乎是西班牙的装束,就像是一堆散布着幻想色彩的票据交换所;当然,理所当然是气候变化和变性问题。但是随后,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等同于一个漏洞:“人工智能与艺术:迈向计算创意”。它的作者拉蒙·洛佩斯·德·曼塔拉斯(RamónLópezdeMántaras)将大部分精力放在音乐上,这是通过计算机“去人性化”的四种艺术中的第一项。 L.A.Hiller和L.M.Isaacson于1957年创作了他们的开创性的弦乐四重奏,使用了1台计算机,该计算机是1952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开发的。它是一个超过180立方英尺的庞然大物,带有2,800个真空管。弦乐四重奏似乎没有进入演唱会曲目,尽管AI生成的音乐仍在讨论中,尽管通常不会进行。现在听到它会很有趣。它会让人想到阿诺德·勋伯格或奥尔本·伯格吗?无论如何,考虑到音乐和数学的密切关系,Hiller和Isaacson的实验不足为奇。
视觉艺术对“非人性化”构成了更大的障碍,但这并没有阻止“知识工程师”尝试。这项努力取得了成功,并于2018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当时在纽约佳士得以超过4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了埃德蒙·德·贝拉米的肖像。污点模糊,散焦的图像令人不安:矮胖的雄性外质体从黑暗,模糊的背景中凝视着,他的止痛药特征丝毫没有告诉我们该人物的人性,他的装束只给人一种模糊的18世纪的味道。这种“绘画”显然是由三名巴黎人组成的集体设计的算法的产物,称自己为“显而易见”。团队并不缺乏幽默感:“肖像”带有“签名”,这是由名为的计算机算法开发的数学公式。
缩写的缩写是“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这是由Ian Goodfellow(三十多岁的博士学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Ian Goodfellow发起的关于“机器学习”的杰出新闻报道发明。对埃德蒙·德·贝拉米(Edmond de Belamy)不满意,他开始扩大家庭,好像是通过自闭症而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家谱树,由两个分支和四个世代组成,有11个成员,每个成员都有所描绘和刻画,都是怪诞的。其中有公爵,男爵,甚至是红衣主教。从埃德蒙的表演来看,这样一批杰出的保姆可能在拍卖会上拍得五百万美元。
佳士得拍卖行并未让埃德蒙的恒星价格受到关注。它的标题是发光的新闻稿,“人工智能是否将成为艺术的下一个媒介?”,结论是:“市场会看到未来吗?看来确实如此。”这不仅是为了促进一种新的商品类别而进行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预示着一个比奥威尔想象的更加黑暗和悲惨的未来。 Acheiropoieta不再是由上面的奇迹般的干预所产生的文物,但是,根据“显而易见的”,这已经成为日常工作:
一方面是生成器,另一方面是鉴别器。我们为该系统提供了从14世纪到20世纪之间绘制的一万五千幅肖像的数据集。生成器根据该集合生成一个新图像,然后鉴别器尝试找出人造图像与生成器创建的图像之间的差异。目的是欺骗鉴别器,使他们认为新图像是现实生活中的肖像。然后我们有一个结果。
瞧,明白了吗?还是结果更类似于均质化和巴氏灭菌的婴儿食品?无味,无色,无形。顺便说一句,“显而易见”如何通过数字化整个Frick艺术参考资料库来收集一万五千张肖像照片?
英国人西蒙·科尔顿(Simon Colton)不乏幽默感,他自identifies为伦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计算创造力教授”。他以名义上的“绘画傻瓜”为名,并将这个角色描述为“建立一个软件系统,这一天有朝一日被视为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始于2006年,这个异想天开的项目产生了看似数量不限的图像,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形式上或形式上的联系,只是斑点的抽象外观。该网站的访问者被定向到“ Amelie's Progress Gallery”,这显然是机敏的Colton的另一项发明。没有为该企业提供场所;它以太“虚拟”地存在于以太坊中,肯定比付房租要好。
如果所有这些异象(或噩梦)都实现了,我们将见证中世纪acheiropoieta的强劲复苏:画笔将从画家的手中夺走,画笔从作家的手中夺走,从演奏者的乐器中夺走,从凿子中夺走来自雕刻家。西欧艺术的光辉轨迹在与波洛克(Pollock)和昆斯(Koons)停顿了片刻之后,将完全屈服于《空心人》(The Hollow Men)中的世界,“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啸叫” —只是那种柔和的呼呼声。将听到计算机硬盘驱动器的声音。在这样凄凉的未来中,十四世纪的塞恩斯艺术奇迹般的,闪闪发光的表面将会出现。鲁本斯和德拉克罗瓦的奢侈气息;被遗忘或深深珍惜和钦佩Ingres肖像的精美釉面?其中存在着一个对我们的文化及其生存至关重要的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