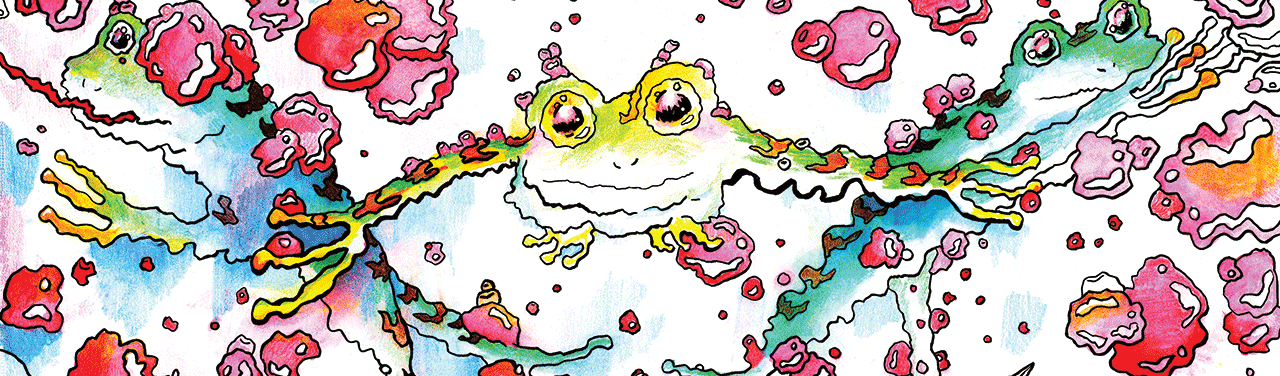当进化具有感染力时
珊瑚微生物学家尤金·罗森伯格(Eugene Rosenberg)在21世纪初遇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工作期间,他发现他无法复制自己十年前的突破性发现。这在当时看起来可能是一次毁灭性的失败,这将引导罗森博格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进化论。
在20世纪90年代,他发现了一种珊瑚疾病的驱动因素。不断上升的海洋温度已经开始导致东地中海的珊瑚漂白。没有人真正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漂白,只知道如果珊瑚虫长时间没有藻类,它可能会饿死。一些人争辩说,息肉之所以会驱逐藻类,是因为在较高的温度下,压力较大的藻类不再对共生做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成了没有生产力的员工,并立即被解雇。
但经过一系列实验,罗森博格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注意到在珊瑚漂白区域的边缘聚集了成团的杆状细菌,这表明受到了感染。如果他先用抗生素处理海水,杀死残留的细菌,然后提高水箱中珊瑚的温度,珊瑚就永远不会漂白。看来,光靠高温并不会导致疾病。细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作用。
他分离出一种名为什洛弧菌(Vibrio Shiloi)的细菌,它是霍乱的远亲,引发了珊瑚疾病。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正常温度下无害,但在条件变暖时会致病。
1996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发现。但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和他的研究生们试图复制这个实验,但失败了-两次。弧菌似乎不再致病。
“珊瑚已经变得有抵抗力了,”罗森博格告诉我。“这是一个打击。”
他开始集思广益,想出可能的解释。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都有适应性免疫系统。接触病原体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学习和记忆。当我们遇到以前见过的病原体时,我们可以在它伤害我们之前将其击退。这就是疫苗背后的原理。但是珊瑚缺乏适应性免疫系统。他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先前接触的豁免权。
有一天,在早晨散步时,罗森博格向他的妻子伊拉娜·泽尔伯-罗森博格提到了这个问题。她是一名微生物学家和营养学家,立刻就有了一个想法:益生菌,一种改善健康的微生物。她解释说,在人体内,本地细菌有助于抵御病原体。这就是为什么服用抗生素的人在治疗后可能会出现新的感染,这是自相矛盾的。消灭共生微生物为机会主义者打开了大门。
也许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实验之间的一段时间里,珊瑚获得了新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现在可以保护它们免受希罗氏弧菌的侵袭。
回到实验室,尤金测试了这个想法。他用抗生素治疗珊瑚,杀死了它们所藏匿的任何微生物。然后,他重复了他最初的实验,将珊瑚暴露在V.shiloi下。现在,当他加大温度时,珊瑚变白了。(一些科学家质疑感染导致漂白,因为他们未能从漂白的珊瑚中分离出这些弧菌。罗森博格说,无效的发现受到方法学缺陷的困扰。他指出,其他研究人员已经证实了他的发现。)。
珊瑚获得的益生菌是什么?罗森博格分离出一种细菌,他将其命名为EM3。当它被引入珊瑚时,就会对什罗氏弧菌产生抵抗力。可能不是偶然的-EM3是一种弧菌,属于一种活动的逗号状细菌,原产于咸水。珊瑚与它们敌人的一位亲戚交上了朋友。这个新的联盟帮助他们适应了不断变化的环境。
罗森博格意识到他偶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生物学原理:适应不是通过基因突变或重组,而是通过微生物调节。在三年的时间里,这种改变发生得非常快,可能在一只珊瑚的寿命内。他的洞察力是,就像传染病可以像野火一样在人群中传播,导致疾病和死亡一样,有益的微生物也可能迅速消散,促进健康和促进生存。
“如果疾病可以流行,”他对我说,“为什么不能进行益生菌流行病呢?”
罗森博格将更广泛的概念称为进化论的“全息组理论”。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杰斐逊在1994年使用的。(杰斐逊说,在多细胞有机体的遗传分析中检测到的微生物不应被视为污染,而应视为所研究有机体的组成部分。)。
独立使用这一术语的罗森博格认为,有机体及其相关的微生物--“全息菌”--是一个单一的进化实体。罗森博格说:“我们认为这是进化中的一种选择水平。”“我与你们竞争的不仅仅是我的基因,还有我的细菌。”
一些人认为,罗森博格研究的珊瑚Oculina patager ica是一种由船只带到地中海的入侵物种。其他人则声称这是一种由于环境变化而扩大活动范围的土生土长的物种。无论哪种方式,它不断变化的流行率都突显了许多人所称的人类世时代的一个生活现实:人类活动没有留下任何生态系统不受影响。这意味着,从珊瑚到青蛙,再到我们,各种生命形式都面临着多重新的选择压力。大规模灭绝是一个有充分理由的担忧。但在这段生物剧变的时期,我们也可能偶尔看到微生物带来的快速适应的例子。自然资源保护者尤其密切关注这些动态,这可能代表着在寻求帮助一些野生动物生存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杠杆点。与此同时,那些研究人类微生物的人已经认为它们是对我们的健康和疾病有贡献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上被忽视的因素。
自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告诉我们,生命不断地受到无数压力的驱使--物种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生物学家们就一直在争论这些变化能以多快的速度发生。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个世纪后,基因组的发现似乎划出了一个上限。动物进化的速度只能与优势基因产生和传播的速度一样快,也只有现有的基因组通过有性繁殖才能重新洗牌。但随后出现了“表观遗传学”:一些适应可以更快地发生,而不是改变基因本身,而是通过改变现有基因转化为活体的方式。
罗森博格和其他人提出了一个更快的过程-有机体可以通过改变它们的共生微生物来迅速适应。使大流行变得如此可怕的特性--快速传染--也可能推动大规模适应。
为了支持全息组理论,罗森博格和其他人将目光投向了对人类微生物群的研究,特别是艰难梭菌的例子。人们往往在住院期间以及在他们用针对另一种感染的抗生素“清除”他们的本土微生物之后感染这种细菌。艰难梭菌随后开花。病人最终可能会神志不清,痛苦不堪,被源源不断的血性腹泻所削弱。据估计,这种微生物每年感染50万美国人,其中约2.9万人在一个月内死亡。
艰难梭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越来越强,因此约五分之一的病例进一步治疗失败。对于这个子集来说,“粪便移植”近乎奇迹。这一过程包括将健康人的粪便通过灌肠或药丸“植入”到艰难梭菌感染者的肠道中。它在治疗艰难梭菌方面有94%的有效率。科学家们认为,它的工作原理是一举恢复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微生物生态系统。捐赠者紧密联系的群体剥夺了病原体艰难梭菌的生态位,将其从肠道中挤压出来。
从技术上讲,粪便移植并不是“益生菌流行病”。但移植表明的原理-本地微生物预防疾病,调整这些微生物可以抵御致命的感染-正是科学家认为可能导致益生菌流行的原因。
从珊瑚到人类,动物是如何获得和培育其微生物群落的,这仍然是个谜。在一些动物中,微生物可能来自父母、同龄人和更大的环境。不同的饮食也会影响微生物区系,这表明一个物种可以容纳的微生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然后是粘液本身,它排斥一些微生物,同时选择性地喂养另一些微生物。
与哺乳动物不同的是,它们的粘膜大多在内部,而珊瑚的粘液在里面和外面都有。但同样的原则也可能适用。研究人员,包括盖恩斯维尔佛罗里达大学的科学家Max Teplitski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珊瑚粘液似乎能吸引和培养特定的微生物群落。致病性弧菌可能是存在的,但在常温下,其他微生物会对其进行控制。然而,当温度升高时,弧菌开始迅速繁殖,压倒了保护性共生体。那就是珊瑚疾病发生的时候。
特普利茨基曾在加勒比海埃尔克霍恩珊瑚中研究过这些动态,他将结果描述为“生物失调”:总是存在的微生物失衡。粉刺、酵母菌感染和蛀牙都是人类非生物疾病的例子-这些疾病不一定是由新到达的病原体引起的,而是由不断繁殖并伤害宿主的微生物引起的。
罗森博格的珊瑚之谜在于它们是如何获得能够在更高温度下保护它们的新微生物的。在珊瑚中,有一些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刻意的过程--不是关于细菌,而是藻类。
在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们提出,在珊瑚在漂白事件中驱逐共生藻类后,它们可能会获得更好地适应新兴条件的新藻类。“这是一个美丽的假设,”罗森博格告诉我。在那之后的几年里,生物学家们观察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加勒比海。
在即将上映的好莱坞电影“我们之间的空间”中,一名美国宇航员在火星上生下了一个孩子。母亲死于分娩,但婴儿幸存下来,并由火星上的一小群宇航员抚养长大。多读。
珊瑚共生体被称为虫黄藻,主要分为四个分支--“A”到“D”。通常,一旦珊瑚从漂白中恢复过来,科学家们就会注意到,最耐热的D分支往往占主导地位。这种变化可能代表的不是细菌的调整,而是藻类共生体更好地适应更高的温度。
为什么这些珊瑚一开始就没有耐热的D分支呢?特拉华大学的研究科学家泰·佩泰(Tye Pettay)说,一个答案是,拥有这一分支的珊瑚可能比拥有其他分支的珊瑚生长得更慢。在他研究的奥比氏菌和珊瑚中,这种生长较慢、耐热的藻类在常温下会招致代价:更容易受到侵蚀力的影响。然而,在高温下,当其他分支开始失效时,D分支的相对劣势就消失了。
随着海洋温度的升高,D分支似乎正在穿过加勒比海--一种在珊瑚体中传播的益生菌藻类浪潮。但是D分支并不能帮助所有的珊瑚。许多专门的珊瑚不能把枝状D带入它们的组织中。这意味着变暖的条件可能会在短期内让大部分多面手珊瑚屹立不倒,因为多面手可以培育D分支。(从长远来看,各地的珊瑚都会面临海洋酸化,这可能比气温上升带来更大的威胁。)。
在D支派的故事中还有一个额外的转折。Pettay最近分析了它的基因组,并得出结论,这种藻类是从一种原产于印度-太平洋靠近泰国的炎热、浅水、经常浑浊的动物黄藻进化而来的。
根据他的分析,帮助加勒比海珊瑚的共生体是一种入侵物种。它是怎么到加勒比海的?佩泰说,压载水是一条可能的路线。
如果这是一波益生菌浪潮,那它就是由人类的双手意外启动的。
佩泰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至少在短期内,这似乎是有益的。”“我不会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我也不会说它是珊瑚礁的救星。”
许多人认为,我们正在经历地球上的第六次大灭绝,这一次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撇开栖息地丧失和过度捕捞不谈,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变化的速度-变暖,人类辅助的病原体传播,以及入侵物种在世界各地的运输。生物学家担心,植物和动物的基因组变化不够快,跟不上。但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微生物可以。
目前还不清楚引起糜菌病(一种有时被比作艾滋病的两栖动物疾病)的真菌来自哪里。研究人员说,它可能来自20世纪初出口用于验孕的南部非洲青蛙;可能来自亚洲两栖动物;也可能来自北美牛蛙。
不管它的起源是什么,随着这种真菌近几十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传播的,尽管它可能是被鸟类传播的,甚至是通过雨滴传播的-它已经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野生动物死亡事件之一。在估计的7000种两栖动物中,有200种已经灭绝,还有500种受到感染。旧金山州立大学生态学和进化学教授万斯·弗雷登伯格告诉我:“对于一种病原体来说,这太多了。”
因此,当弗雷登伯格在本世纪头十年注意到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山脉研究的一些两栖动物在龟裂的袭击中幸存下来时,这是有意义的。他想知道,这些人与那些死去的人有什么不同?
在佛罗里达的一次会议上,他发现了一条线索。一位名叫里德·N·哈里斯(Reid N.Harris)的生物学家做了一次关于火蜥蜴的报告。他问为什么一些物种成群筑巢,而另一些物种单独筑巢。他的研究使他得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解释。群体筑巢的物种共享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不会导致疾病,而是保护它们的卵不受病原真菌的侵袭。换句话说,它们筑巢在一起是为了共享一种益生菌。
谈话结束后,弗雷登堡追上了哈里斯。保护性微生物能解释他在内华达山脉看到的抗药性动物吗?这两位科学家开始合作。结果发现,耐chytrid的青蛙-Vredenburg研究了山地黄腿蛙Rana Muscosa-倾向于藏有一种特别的微生物,称为淡黄色简氏杆菌(Jansinobacterium Lividum)。微生物产生抗真菌的代谢物。它不能完全防止感染,但似乎抑制了真菌的过度生长。从本质上讲,赤霉菌把潜在的病原体变成了无害的共生体。
结果,内华达山脉发生了一种奇怪的自然选择。当壶菌席卷山区时,携带这些微生物的个体往往会存活下来。壶类大流行是基于它们的微生物来选择青蛙-在一次选择性的扫荡中,拥有一个微生物群落的两栖动物在所有其他微生物群落中幸存下来。
当然,这不是罗森博格在“珊瑚”中描述的那种“益生菌流行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两栖微生物群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但目前还不清楚弗雷登堡的青蛙是否在一代人中获得了新的微生物。
问题是,弗雷登堡会故意引发益生菌流行吗?他能通过加速自然发生的事情来拯救青蛙吗?
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因为与需要给所有人接种的疫苗不同,微生物是自我繁殖的。一旦它们“粘在”一只青蛙身上,理论上它们就可以传播给其他青蛙。如此获得的一种抗壶菌微生物可能就像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疫苗。
出于同样的原因-活着的微生物可以不受控制地传播-弗雷登堡非常谨慎地进行着。他和他的同事们确定了一种青蛙种群,这些青蛙种群仍然不存在栗虫,从已经携带这种细菌的个体中分离出来-排除了引入新疾病的可能性-然后在大桶中培养这种细菌。
在此期间,真菌到达了。第二年,当弗雷登堡回到山上时,他只发现了120只青蛙。他治疗了三分之二的人,将每个人分别在细菌酿造中洗澡,而留下了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治疗。
一年后,也就是2011年,当他重新探访这些动物时,只有接受治疗的个体还活着。
“我不会只是挥舞着胜利的旗帜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他告诉我。“我们仍然不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确切机制。”(经过处理的青蛙在第二年冬天死亡,不是死于虱子,而是因为干旱减少了它们过冬的池塘。他们僵住了。)。然而,Vredenburg是乐观的。
他指出,作为一个类别,两栖动物有3.6亿年的历史。它们在四次大灭绝中幸存下来。“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感染致病真菌了,我保证,”他说。微生物可能以前救过它们。
要使一种性状在进化过程中提高适合性,它必须在世代之间传递。全息组观点--微生物和宿主构成一个单一的进化单位--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微生物并不总是像传家宝一样在世代之间传递。如果它们不是,那么全息生物真的会随着进化时间的推移而存在吗?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南希·莫兰(Nancy Moran)认为,推动全息组概念泛化的努力存在概念上的草率。她同意微生物可以改善宿主的健康状况,甚至可以推动进化。她自己对豌豆蚜虫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她指出,蚜虫耐受温暖温度的能力取决于它们所携带的细菌共生菌的种类。
但她说,这些关系必须得到证明,而不是假设。微生物之间相互竞争,而欺骗--从一段关系中获得的比你贡献的更多--是一种可行的生存策略。一些微生物必然会采用它。因此,宿主和微生物之间的和谐,甚至动物微生物区系成员之间的和谐,并不是既定的。仅仅因为发现了附着在宿主上的微生物并不意味着它有助于健身。它可能是一种寄生虫,或者仅仅是路过。“当然,很明显,其他生物也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说。“但从那里到全息组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它们加在一起是一个选择的单位。”
与此同时,全息组概念的支持者试图证明微生物可以驱动物种形成。在一项实验中,特拉维夫大学的罗森伯格和他的同事们将果蝇分成两组。他们给每组人喂食不同的食物-糖蜜或糖-然后在几代之后让这些果蝇团聚。虽然在基因上仍然相似,但这些苍蝇现在更喜欢只与它们之前群体的成员交配。他们怎么知道有什么不同呢?当科学家用抗生素治疗果蝇,消灭它们的微生物时,它们就失去了这种偏好。推动它们分化成不同物种的是果蝇的微生物群,而不是它们的基因。
事实上,许多动物确实会在世代之间转移微生物。各种各样的哺乳动物幼崽,从大象到马,都会吞食父母的粪便,这一做法被称为粪便吞噬。考拉妈妈更进一步:它们会产生一种名为“纸”的特殊粪便,供幼崽在断奶时食用,这种粪便是消化桉叶所必需的微生物的遗留物。
人类并不是很明显是共食性的,但即使我们把微生物传给了我们的后代。婴儿在通过产道时会从他们的母亲那里得到一块钱。母乳喂养既能培养出某种叫做双歧杆菌的微生物,又能给婴儿带来更多的细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哺乳的母亲会将独特的、家族性的细菌菌株传递给她们的婴儿,这表明,就像那些蚜虫一样,人类也可能会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