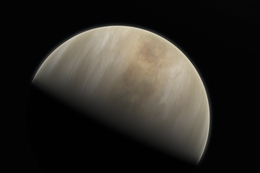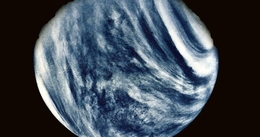论生命的使用
在黑客新闻最近的一次讨论中,一位评论者提出了以下问题:好的,那么,我们对Tarsnap有什么看法?这家伙显然是个天才,他把时间花在备份上,而不是解决千年问题。我怀着最大的敬意这么说。创业这件事是不是一个陷阱?
我考虑过在帖子中回复,但我认为它值得一个深入的回答-而且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而不是在100+评论帖子中回复。首先,省去哲学上的争论:是的,这是我的生活,是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或者浪费--它;但我不认为询问这是否是我的时间的最佳消遣方式有什么不对。如果问题不仅仅是关于我所做的选择,而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加倍适用:我们的社会结构是否鼓励人们做出的最大贡献低于他们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这就是说,我确实有点反对这个问题的前提-特别是关于我把时间花在备份上的说法。一方面,这是真的:自2006年以来,Tarsnap一直是我的全职工作。我偶尔做咨询工作--早年比最近做得更多--但从财务上讲,这只是个舍入误差;支付账单的是Tarsnap(包括让我买下我将于下周搬进的房子)。另一方面:我在Tarsnap上的工作已经相当大地扩展到了邻近的领域。在2009年,有许多用户要求使用受密码保护的Tarsnap密钥文件,并且确定当前基于密码的密钥派生技术非常缺乏,于是我发明了SCRYPT-在这个过程中,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密码学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发明了SCRYPT-在这个过程中,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密码学领域。当然,我这么做是因为这是我可以做的让Tarsnap更安全的事情;但把它放在把我的时间都花在备份上的保护伞下就有点牵强了。2011年,为了将不同主机上的守护程序安全地连接在一起,并且对现有的基于TLS的选项不满意,我编写了SPIPED。虽然我认为KIT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但我毫不道德地认为它对计算机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就像Scrypt一样,虽然我创建它是为了满足Tarsnap的需求,但将这样一个通用的开源工具放在致力于备份的狭隘保护伞下将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做法。大约在同一时间,我开始开发kivaloo,这是我的高性能键值数据存储。这可能是我编写的所有软件中使用率最低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其他人在使用ITAT(尽管它是开源软件,不一定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认为它是我最好的代码之一,我认为未来它可能会被用于更多的领域,而不仅仅是Tarsnap。从2006年开始,并在亚马逊于2012年推出支持HVM的EC2系列实例后显著加速,我一直在创建和维护FreeBSD/EC2平台。虽然我没有任何关于其使用情况的准确统计数据,但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云中运行FreeBSD的人中有44%使用亚马逊EC2;所以-尽管目前只有22人为我的努力提供赞助-但很明显,我在这里的工作卓有成效。同样,当我因为想要在EC2中为Tarsnap运行FreeBSD而致力于此时,我不认为它可以完全归入处理备份的类别。当然,手头的问题不是我是否做了什么有用的事情,而是这是否是我度过这些年的最有用的方式。从提到千年问题来判断,我想他们脑海中的具体选择是从事研究事业;事实上,在我在已故的彼得·博尔文(Peter Borwein)手下攻读数论本科课程和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之间,我可能曾考虑过,如果我的生活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我可能会认真研究伯奇和斯温纳顿-戴尔猜想(Birchand Swinnerton-Dyer Conjection)。(一个与我目前参与的BSD非常不同的BSD!)。那为什么我不是学者呢?影响因素很多,创办Tarsnap当然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数因素可以概括为学术界是进行新奇研究的好去处。2005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在多线程CPU中使用共享缓存作为加密端通道的文章,2006年我希望继续这项工作。最近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了加拿大的家乡,我有资格获得加拿大国家科学和工程研究理事会的博士后奖学金,所以我申请了。我没有得到它。我的上级告诫我做一些年轻学者时过于新奇的工作的风险:委员会不知道如何看待你,而且他们没有任何声望可以依靠。事实上,我在自己的渠道攻击中遇到了这个问题: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