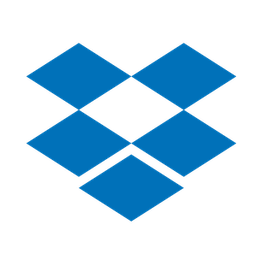咖啡锈
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咖啡树应该是安全的。但是真菌发现了它们。
在危地马拉的圣佩德罗·耶波卡帕(San Pedro Yepocapa)山城外,埃尔默·加布里埃尔(Elmer Gabriel)的咖啡树应该是枝繁叶茂、熠熠生辉。现在距离圣诞节还有一周,这是咖啡收获季节的核心,如果他的灌木丛健康的话,它们看起来就像挂着装饰品的假日树,点缀着鲜红的咖啡樱桃。但在他陡峭的田地一侧延伸的一排长长的队伍中,植物已经枝繁叶茂,枯萎了。它们的大部分叶子都不见了,剩下的是淡黄色的橄榄色,边缘卷曲着。在树叶的上表面有黄色的斑点,中间是棕色的。它们的底面是鹅卵石的,上面覆盖着一层细小的橙色灰尘。
灰尘看起来像一块钢铁上的铁锈,这就是它的名字的由来:这些植物感染了咖啡叶锈菌,一种毁灭性的真菌。加布里埃尔一看到问题就意识到了。铁锈,西班牙语中的la roya,大约在十年前到达,大约在他买下被他称为Finca La Felicida的山顶地块的时候,也就是“幸福的农场”。他从小就知道这件事: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咖啡农场主,在20世纪70年代,锈病侵袭,使他们的植物变得干燥。他的父亲在植物上喷洒了杀菌剂,疾病就消退了。十年前,当锈病再次出现并在拉费利塞达的灌木丛中出现斑点时,加布里埃尔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疾病再次消退。
但是现在杀菌剂不再像以前那样起作用了。“拉罗亚不尊重他们,”加布里埃尔通过翻译告诉我。有一天,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一株植物的几片叶子上的金点开花了。加布里埃尔喷了一次,又喷了一次,但是斑点变宽了,然后变得又黑又干,从中间裂开了。树叶变脆了,在边缘卷曲,当微风推搡它们时,它们从植物上掉了下来。灰尘,真菌孢子,漂浮在田野上,感染了另一棵灌木,或者落在地上,下雨时溅到了下一棵植物上。植物缓慢死亡的循环又开始了。
盖伯瑞尔不舒服地耸了耸肩,他穿的马球衫在他的耳边扎成一团。“我以为一两年后它就会消失,就像以前一样,”他说。“但它完全侵袭了…。尽管使用了杀菌剂,但似乎还不够。“。
由于没有叶子,植物没有能量开花和结实,果实是隐藏在咖啡豆核心的鲜艳的肉质樱桃。没有水果,就没有庄稼,也没有收入来购买更好的杀菌剂,或者用健康的植物取代垂死的植物。在咖啡树上长出雀斑的斑点中,加布里埃尔瞥见了他生计的终结,以及他将土地和知识传给儿子的希望的破灭。
在这种痛苦中,加布里埃尔并不孤单。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数以万计的小农场里,咖啡树在锈病的侵袭下步履蹒跚。在一些地区,超过一半的咖啡种植面积已经停止生产。从2012年到2017年,锈病造成了超过30亿美元的损失和利润损失,迫使近200万农民离开了土地。
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谈论一种植物疾病可能看起来很无聊。但在世界各地,1亿人从咖啡中获得尊严和收入,咖啡是世界上交易量最大的农产品之一。咖啡是小城镇和小农户的生命线,这些地区土壤稀薄,森林茂密,陡峭,无法种植更多其他作物。
随着农民们耗尽了抗击咖啡叶锈病的资金-气候变化降低了将植物重新安置到更安全的土地的可能性-科学家们正试图削弱这种疾病的威力。但他们重新培育植物和再培训农民的努力面临着漫长的毁灭历史:对这种疾病的第一次警告,以及对其破坏性的第一次证明,可以追溯到150多年前。
O英国出版物“园丁编年史和农业公报”上出现了一则简短的通知,描述了一种以前没有人见过的植物病原体。“我们最近收到了…。这是一个在锡兰咖啡种植者中引起了一些恐慌的A样本,因为它似乎在锡兰的咖啡种植者中取得了快速的进展,“便条上写道。
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是殖民地领地,自1815年以来由英国控制。荷兰商人将咖啡进口到锡兰,英国人将咖啡作为种植园系统和贸易帝国的基础。这个殖民地生产的咖啡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就在“园丁纪事”上的通知发布十年后,所有的通知都不见了。
玛丽·凯瑟琳·艾梅(Mary Catherine Aime)告诉我:“这是一场可怕的、毁灭性的流行病--农作物损失了90%,100%。”她是普渡大学植物学和植物病理学教授,也是该校植物和真菌馆藏的负责人。“从那以后,我们就把咖啡运到世界各地,让它远离疾病。”
到19世纪末,锈病已经摧毁了南亚和东亚的咖啡种植。锡兰的殖民地种植园重新种植了茶叶,使英国人变成了喝茶的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种植园则种植了橡胶树,这些橡胶树是一位英国探险家从巴西走私出来的种子。咖啡种植跨越大西洋。在美国农业部1952年绘制的地图上,一条深色虚线在本初子午线将世界分开。东部的一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阿拉伯半岛、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都用大写字母贴上了“患病”的标签。西面的一切-中美洲和南美山脉的气候模仿了曾经盛产咖啡的凉爽高地-都被坚定地命名为“没有生病”。
人们自信地认为咖啡锈不能越过大西洋的警戒线。那是不对的。没有人能说出锈病是如何来到美洲的。它可能是以其他植物的运输方式运抵的,无论是活的还是干的。它可能会粘在旅行者的鞋子或衣服上。锈病甚至有可能在高海拔风中穿越地球,另一种植物病害小麦茎锈病就是通过这条路线在各大洲之间传播的。咖啡锈菌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移动,然后在1970年,它的显露斑点和充满孢子的灰尘出现在巴西的咖啡树上。它迅速向西传播,然后向北传播: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然后向上穿过中美洲-第一波浪潮,加布里埃尔记得他父亲时代的第一次浪潮。这种疾病很凶猛,但当它出现时,大量使用杀菌剂和对植物的精心管理使它得到了控制。
然后,在2008年,锈菌在哥伦比亚爆发,就像150年前在亚洲一样毁灭性地爆发,到2012年,它已经转移到中美洲。就像它在锡兰发生的那样,它摧毁了整个农场。
艾梅是一位世界知名的锈菌专家,他是为数不多的研究这一巨大领域的真菌学家之一:大约有8000种已知的锈菌,比所有其他植物病原体的总和还要多。她一直负责鉴定一系列新的锈菌种类,自从咖啡叶锈病在拉丁美洲激增以来,她一直在竭力了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让一种由农用化学品控制的低发病率疾病逃脱了这种控制,并发动了一场世界末日般的袭击?
起初,她和其他研究人员想知道咖啡锈菌是否发生了变异,改变了它的基因构成,使其成为更具毒性的有机体。但在她的研究中,艾梅一直在构建一份有效的咖啡叶锈病遗传图谱,由数千个真菌样本的基因组分析组成。在这些数据中,她没有发现咖啡锈的成分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应对的,”她说,“是气候变化的影响。”
她总结说,发生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天气-更炎热,更猛烈的降雨,更高的持续湿度-创造了使咖啡农场变得更加友好的主人的条件。2012年,中美洲各地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降雨反复无常,倾盆大雨。这些现象一起使锈菌在其繁殖过程中更快地循环:感染植物的叶子,产生孢子,释放孢子,并找到新的植物生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艾梅说。“这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
在圣佩德罗·耶波卡帕(San Pedro Yepocapa),我问加布里埃尔,他是否考虑过为什么铁锈变得更严重了。他用农民为城里人保留的礼貌和耐心看着我。
“雨下得更大了,”他说。“旱季,时间更长,风也大得多.”他又耸了耸肩,似乎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
这在很多方面都像正在展开的冠状病毒大流行。有警告。有一种信念认为,美洲不会受到影响。人们有信心现有的工具可以管理这一威胁。但最深的相似之处可能是,就像冠状病毒一样,每种疾病的负担都落在那些最负担不起的人身上。对于冠状病毒来说,那就是城市居民几乎没有储蓄,没有第二个家可逃,依靠公共交通去上班养家糊口。说到咖啡锈,那就是农民。
世界上90%以上的咖啡来自贫穷经济体的小农场:由单一家庭拥有或租赁的财产,种植的是单一作物。与此同时,咖啡的批发价暴跌,迫使农民和他们的家人在农场外寻找工作,而此时他们的农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应对锈病的加剧。
喷锈抑制其开花有一种并行控制策略。也就是说,寻找对病原体具有一定内在抵抗力的咖啡品种,并对它们进行杂交,以生产出不太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新品种。要想看到这种方法的潜力,你只需走到加布里埃尔球场的另一边。那里的植物枝繁叶茂,光泽健康,点缀着鲜艳厚重的樱桃。身穿清爽衬衫的高个子罗德里戈·查韦斯(Rodrigo Chávez)蹲下身来,轻轻地摩擦着一片树叶,寻找能揭示真相的斑点。加布里埃尔挥舞着双手,兴奋地用西班牙语和他交谈。
“他把它叫做超市,”查韦斯告诉我。“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哪里正在开花,那就是明年的收成。他很高兴庄稼长得这么好,这会给他带来更高的收入。“。查韦斯拂去双手的灰尘,站了起来,看着更多像我们站在旁边的灌木丛一样的行列。“他特别高兴,因为他不必喷洒这些植物,”查韦斯继续说。“因此,他花了更少的钱来管理它们,而且他会有更多的收入。”
查韦斯是健康的植物和锈病的植物在同一片土地上的部分原因。他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诺曼·博洛格国际农业研究所的项目主任。该研究所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资助下,运营着中美洲弹性咖啡项目,将抗锈杂交品种带给农民-实际上是带给农民的,而不仅仅是在研究站测试地块。三年来,团队成员-德克萨斯州的查韦斯和该项目的地区主任罗杰·诺顿(Roger Norton),以及萨尔瓦多的路易斯·阿尔贝托·奎勒·戈麦斯(Luis Alberto Cuella Gomez)、奥斯卡·拉莫斯(Oscar Ramos)和丹尼尔·杜邦(Daniel Dubon)-一直带着教育材料和植物徒步穿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他们已经说服了100多名小农户在他们现有的植物旁边种植新的咖啡样本,并观察新植物对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可预测的条件做出的反应,并向团队反馈。
该团队给农民带来的植物是由研究机构生产的咖啡遗传学的复杂混合物,这些研究机构以法国的CIRAD、哥斯达黎加的Catie和洪都拉斯的IHCAFE等缩写闻名,这些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作。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期间,它们是由政府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国际慈善机构赞助的强大的国家咖啡研究所网络中的剩余部分,当时德克萨斯州研究所的同名人物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g)正通过培育小麦抗锈病来避免国际饥荒。这些研究机构和其他机构生产了许多现在生长在拉丁美洲田地的植物,这些品种是专门培育出来的,一旦跨越大西洋就能抵抗锈病。
自国际农业合作第一次开花结果以来的几十年里,迫使人们重新评估博洛格的遗产:他的高生产率杂交种养活了数百万人,但它们对水和外部营养的需求推动了大坝建设、地下水开采和化肥使用量的大幅增加。20世纪的最后25年对咖啡机构也不友好。像巴西这样的大国能够维持他们的国家研究计划。但在较小的国家,内乱和崩溃的经济迫使政府就将有限的收入花在哪里做出艰难的决定。就在锈病开始卷土重来的那一刻,资金短缺让农民们缺乏科学支持。
全球研发非营利组织“世界咖啡研究”(World Coffee Research)的首席执行官詹妮弗·“弗恩”·朗(Jennifer“Vern”Long)说:“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培育出来的第一代抗锈品种正开始失去抵抗力。”“Vern”Long是一家全球研发非营利组织“世界咖啡研究”(World Coffee Research)的首席执行官。“要让他们全部失败还需要一段时间,但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她补充说,依靠近交系抗性来保护作物的农民现在必须购买和施用更多的化学品,并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监控他们的田地:“以这种方式管理农场的成本要高得多。”
世界咖啡研究中心和得克萨斯研究所,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支持下,代表了博劳格时代遍布世界各地的研究基础设施的一种重建。他们与感兴趣的公司合作:德克萨斯集团与瑞士跨国企业雀巢(Nestlé)(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买家)和挪威化肥公司Yara;World Coffee Research与许多最大的咖啡零售商,包括星巴克(Starbucks)、拉瓦扎(Lavazza)、雅各布·杜威·埃格贝茨(Jacobs Douwe Egberts)和福尔杰斯(Folgers)的母公司。与德克萨斯小组形成对比的是,世界咖啡研究组织还支持实验室工作,包括艾梅的基因组分析。
这项研究不能操之过急--即使现在全球变暖正在改变天气--因为开发能够可靠繁殖的新咖啡品种需要数十年的时间。研究人员的目标和农民复杂的需求是相互竞争的。农民们仍然希望相信他们种植了多年的植物,即使这些咖啡正在倒闭。科学家们希望迅速培育出有弹性的植物,即使他们知道采用可能需要时间。
可能需要25年的时间才能将咖啡树杂交成一种新的类型,并通过重复的世代来试种新的植物,以确保它的品种是真实的。锈病蔓延地区的农民没有那么多时间。为了加速替代,世界咖啡研究公司一直在支持所谓的F1杂种的开发,这是来自不同基因的亲本的第一代杂交,可以在10年内准备好在田间种植。
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虽然杂交种生长旺盛,但它们的繁殖是不可预测的-因此,用相同的植物取代植物的唯一方法是从苗圃或公司购买一株,而不是从原始植物自己的种子中种植。这意味着,目前正在开发的混合动力车在使用年限结束时需要更换为新购买的车型。
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将是农民的负担。但世界咖啡研究公司将杂交作物视为长期战略的一部分--艾梅在寻找生产力和抗性的分子标记方面的工作可能导致培育出全新的咖啡树品种。然而,与此同时,加快将更好的咖啡运往农民田地的时间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低价、锈病恶化和奇怪天气的经济紧缩正在对咖啡田造成压力。
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诺顿告诉我:“许多农民基本上是通过消耗自己的资源来生存的。”“他们没有给家人的劳动定货币价值。”
面对枯萎的植物和没有收入支付重新种植的费用,世世代代种植咖啡的家庭离开了他们的田地。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向北走。2018年10月至2019年5月,当移民穿越美墨边境被捕时,危地马拉是大多数人的原籍地。
德克萨斯A&M项目希望避免农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要找到适合不同领域的新杂交种和新品种,需要农民和与他们合作的研究人员对微型生态系统的错综复杂进行细粒度的研究。与此同时,研究人员正在教农民如何最好地维护新植物,并帮助他们识别额外的作物,如柠檬草,这些作物可以在咖啡树中种植,以获得额外的收入。诺顿说,他们已经收到了参观过示范田的生产者的来信,亲眼看看他们的邻居是如何从新的杂交车、免费化肥和专家的建议中受益的。他们叫嚣着要自己种植新的版本。
不过,这些植物能起到多长时间的作用可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路易斯·佩德罗·塞拉亚·萨莫拉(Luis Pedro Zelaya Zamora)是他家族的第四代人,领导着咖啡生产商贝拉·维斯塔(Bella Vista)。他向我描述了气候变化和锈病的无情发展,距离La Felicida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当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罗亚就一直在这里,”他说,“但它从未登上过1000米以上的高山。然后,大约8年前,你开始在1200米处看到它,然后是1500,1600,1800。每年它都会涨得更高,直到到处都是。从那以后,它就变得非常咄咄逼人。“。
Bella Vista的意思是“美丽的景色”,这是一个准确的描述:一个对称的火山锥从这家人的田野上升起。从农场办公室外的阳台上,你可以看到火山口顶端优雅的曲线。这一景象提醒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山是尽头的。如果逃避气候变化的唯一方法是将作物移到更高的海拔,那么在某个时候,海拔就会耗尽。
塞拉亚还将他的一些财产交给了德克萨斯项目分发的混合动力车测试。疾病和温度之间的挤压让他清楚地意识到,确定他们可以种植的最抗锈、最具弹性、最高产的植物是多么紧迫。塞拉亚估计,处理铁锈的成本相当于他每公顷产量的五分之一。他说:“支付成本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生产率。”“如果你的生产力很低,它会把你消灭的。”
它的目的是减缓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疾病的发展,但气候变化正在威胁这种多样性的来源。
咖啡如此容易受到锈病的威胁,以及更容易受到锈病侵袭的变幻莫测的天气的挑战,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基因范围很窄。它不完全是一种单体作物-例如,不像香蕉,世界各地的香蕉都是彼此的克隆,可能会被一种单一的疾病消灭。(事实上,我们今天吃的叫做卡文迪什的香蕉,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一种更甜的品种格罗斯·米歇尔(Gros Michel)被一种真菌疾病消灭而被开发出来的。)。尽管如此,咖啡品种之间的关系还是足够密切的-一个可能是虚构的故事将美洲所有的咖啡都追溯到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