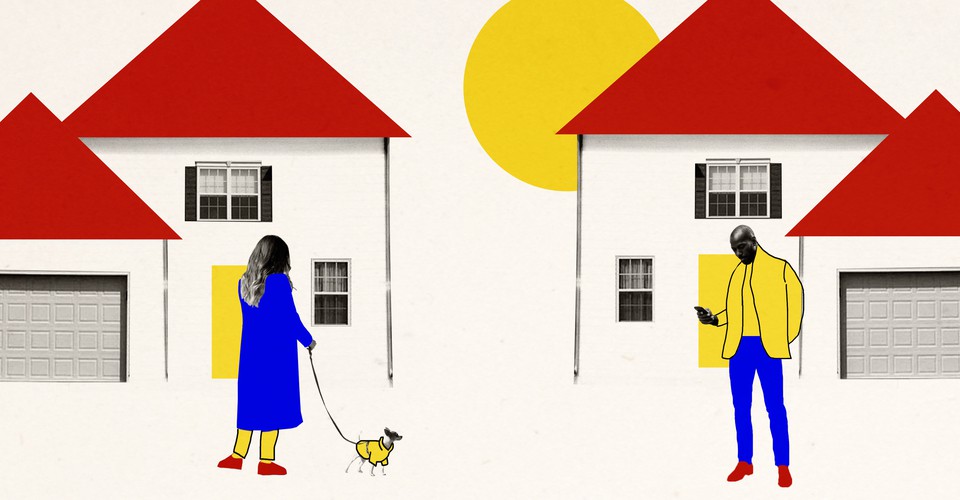郊区的复仇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未知”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正在离开的世界的系列,也是一个被大流行重塑的世界。
我在Windy Corner,这是一处舒适的庄园,位于伦敦郊外一块彬彬有礼的飞地上。郊区一如既往地令人愉快:邻居们很友好,环境没有城市的噪音和污垢,非常适合孩子们。她的父亲建造了这座房子,他为将自己的家庭置于“可以获得的最好的社会”中而感到自豪。
但霍尼彻奇发现这些人很枯燥,他们的抱负也平淡无奇。邻居们都很和蔼可亲,但用她的话说,他们的“相同的兴趣和相同的敌人”变得令人窒息。她总结说,郊区实际上是一个恐怖的地方。
霍尼彻奇可能是一名千禧一代布鲁克林人的媒体专业人士,为在当地胃部酒吧启动内格罗尼季节做准备,或者是一名活动人士,反对当地的NIMBY,反对密度更高、交通和骑自行车友好的填充物开发。但事实并非如此,她是E·M·福斯特(E.M.Forster)1908年小说“一间可以看到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中的主人公,这部小说尖锐地批评了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生活,包括郊区单调乏味的生活。
到福斯特写作时,人们嘲笑郊区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在中世纪晚期,欧洲郊区的农业和商业农民大多被视为城市绅士的下层阶级。18世纪伦敦的玛丽尔伯恩、梅费尔和其他社区延续了这一传统。1897年,赫伯特·G·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大战”中的火星人在郊区开始了他们的愤怒,那里的生活被认为是如此悲惨,以至于连外星人都赢得了第一次打击。这种蔑视依然存在:1962年,马尔维娜·雷诺兹(Malvina Reynolds)在一首关于千篇一律的房屋的流行歌曲中唱道:“小盒子,尽管如此。”今天,同样的冷嘲热讽依然存在。
然而,人们一直热爱郊区生活。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城市一直在边缘发展。风之角那种的乡村生活演变成了20世纪初的“有轨电车郊区”,从城里乘马车就能提供舒适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房地产危机的迫使下,种族主义的政府住房补贴、白人逃亡和北美大陆的巨大面积助长了大规模开发的分区。就像色情作品一样,当你看到郊区时,你就会知道它是一个郊区:大片低矮的建筑,那里的住宅和商业是分开的,那里几乎没有工业,家庭生活在独立的住宅里蓬勃发展,这些住宅点缀着蜿蜒的街道,两侧是草坪,信箱点缀着。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即我们中的1.75亿人,现在生活在这样的社区里,大多数原因与我们的祖先相同。
或者我们生活在一个稍微城市化的地方,因为现在,到处都是郊区。84%的美国人生活在城市,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生活在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的密集、现代主义的城市空间里-比如纽约或香港。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占据了休斯顿、亚特兰大或丹佛等更大的大都市地区,这些地区远远超出了城市边界。总体而言,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住在独栋住宅里,这提醒人们,即使是达拉斯或凤凰城等美国大城市的市中心,也穿着郊区的装饰品。
几十年来,城市学者一直在寻求结束美国与无序扩张的长期婚姻。建筑师艾伦·邓纳姆-琼斯(Ellen Dunham-Jones)和琼·威廉姆森(Jun Williamson)已经确定了值得翻新的郊区形态特征,包括低密度建筑占主导地位,强调私人空间而不是公共空间,依赖单一用途而不是混合用途的分区,几乎完全依赖汽车,以及让街道网络用处变得不那么有用的死胡同。
但在经历了令人焦虑的2020年春天之后,这些缺陷似乎成了新的奢侈品。在一块属于你自己的土地上的一栋大房子里,总能找到一种舒适的感觉。随着一场大流行降临到你身上,你的解脱更是令人欣慰。随着新型冠状病毒从严重的恐惧转变为长期的萎靡不振,城市居民被困在几乎没有户外空间的小公寓里,依赖公共交通,而现在公共交通似乎不太像是一项公共服务,而更像是一个滚动的培养皿。与此同时,郊区居民在大片私人地块上散布的房屋的安慰中保护了他们的家人,这些房屋与邻居分开,只有乘坐私家车才能安全到达。他们在许多卧室里躲避着病毒的侵袭,睡得很香,怀着新的信心梦想着美国梦。
这是郊区的灵魂。美国梦有时被等同于拥有房产,核心家庭拥有这样的房产-但实际上,它们只是一个更根本的郊区愿望的外壳:个人主义,郊区的房子界定了个人主义,然后加以保护。
“美国梦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城堡,”俄亥俄州立大学诺尔顿学院建筑系主任托德·甘农(Todd Gannon)告诉我。最重要的是,郊区生活是一种独立的生活,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园,美国家庭可以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潜力,不受其他人的干扰。即使是家用汽车也有自己的卧室。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独立总是虚构的。郊区产生的税收基础往往不能支持维持它所需的基础设施-道路、下水道、学校、紧急服务,以及所有其他设施。加上联邦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利息扣除,郊区的生活方式相当于政府的巨额补贴,否则它就会慢慢衰败失修。
郊区制造了物质自给自足的错觉。即使是与它联系最紧密的建筑设计,美国的牧场住宅,也从自治的幻想中借用了它的名字和风格。牧场宽阔而杂乱无章,将真正的西部牧场变成了一系列象征:提供机会的广阔开阔空间;掌管这片土地的家庭,因此它自己的命运;甚至是牲畜的良好饲养,现在已经转变为养育孩子。
当美国梦被框定为独立而不是共产主义时,城市生活的好处开始看起来反而是有害的。例如,在城市环境中,可步行将人们与当地商业联系起来-一些单一用途的住宅分区避免了自驾游。这就是为什么建筑师安德烈斯·杜尼(Andrés Duany),也是新城市主义国会的联合创始人,将独户住宅社区比作“未做的煎蛋卷”,鸡蛋、奶酪和蔬菜代表着家庭、工作和商业,这些东西不自然地相互分离。相比之下,混合用途开发项目提供了距离公寓和公寓一箭之遥的商店、餐馆和办公室。
但拒绝混合用途规划,让郊区社区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头几个月出人意料地具有弹性。当场所因避难所就地命令而关闭时,能够走到拐角的咖啡馆吃早午餐(大概是煮熟的煎蛋卷)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尽管餐厅和零售商重新开业,但在餐厅就餐或购物已经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餐厅入住率受到社会距离的限制;机构难以维持收支平衡;对封闭的空调空间污染的担忧破坏了体验。所有这一切最终可能会恢复正常,但到那时,胃部酒吧和冰激凌店可能已经倒闭了。咖啡店可能会永久改建成没有桌子的提货摊。商业灾难对现有混合用途开发项目吸引力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单一用途、低密度的住宅社区,后者从来不依赖这些好处作为居住条件。
城郊生活,也许是以持久的方式。以汽车通勤为例:大量离开办公室的人大幅减少了交通和污染,如果即使只有一小部分放弃通勤的人继续在家工作,这一趋势也将以某种形式继续下去。邓纳姆-琼斯也是我在佐治亚理工学院设计学院的同事,他认为,即使远程办公的人数略有增加,也可能会增加当地步行和骑自行车旅行的吸引力。一家人有两辆车,但无处可去。他们正在重新发现步行者的乐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郊区居民想要城市生活的密度。一些人担心这一点,将病毒的传播归咎于拥挤的大都市民众。这些恐惧将拥挤误认为密度。一些最严重的冠状病毒热点不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爆发,而是在拥挤的社区爆发,如疗养院、哈西德家庭和制造工厂。像首尔和新加坡这样人口稠密的全球城市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病毒。与此同时,在纽约市地区,某些郊区的早期感染率更高。
但美国不是韩国或新加坡。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在逃避密集的垂直设计。那些已经喜欢过简朴生活的人很可能会利用对新冠肺炎的恐惧来巩固自己的偏好。
至少,在大流行后的世界里,他们家的室内设计可能会发生变化。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牧场别墅可能看起来很自然,但它是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设计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个牧场是由一群杂乱无章的工作人员拼凑而成的,他们的来源和灵感都不太可能。它的内部设计结合了欧洲高现代主义的极简主义(受另一场疫情-结核病的影响)、西班牙牧歌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驯服的自然主义,他的尤森式住宅设计和郊区乌托邦的愿景在公共规模上弘扬了个人主义。
牧场经常将就餐和生活区融合在一起,这种设计将演变成现在无处不在的大房间。但他们的室内设计也借用了一些花花公子牧场的视觉和象征性装饰-卧室和洞穴里的所有木质镶板,厨房橱柜上的,或者大教堂天花板上裸露的横梁上的所有木质镶板。就连烧烤架也部分改编自西部牧场,在加州早期的一些设计中,烧烤架被建造成厨房或庭院。
像烧烤这样的便利设施提供了更多享受呆在家里的理由。现代化的电动住宅,有冰箱、洗碗机和洗衣机等,有助于将以前需要外部接触的活动,如洗衣或每日送牛奶,整合到家里进行的努力中。这些设备锚定了性别规范,发明了越来越多的新劳动力来填补节省的时间-但它们也强化了在家里实现更多需求和欲望的倾向。一种新的小玩意儿或电器(以及容纳它的空间)会产生更大的自给感,也更有理由寻找更多的空间和更多的小玩意儿。郊区的房屋持续增长,部分原因是它们内化了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
现在房主们正在进一步装备他们的私人飞地,有后院的度假地和豪华的游泳池度假村,不确定冠状病毒的威胁会持续多久。冷柜也已经销售一空,因为有空间容纳它们的消费者寻求更好地做好准备,以防未来的病毒激增将他们推回冰箱内。由于供应问题和肉类加工厂爆发的肉类短缺的威胁,冰柜变得新的必不可少。(从诗意上讲,它们还恢复了美国牧场之家与实际牧场的历史联系,那里有大量的牛,因此牛肉也很丰富。)。那些有能力、有空间、有文化倾向的人可能会让囤积食物成为一种主流做法,而不是偏执狂的边缘神经症。在20世纪90年代末,旧酒窖演变成了郊区的酒室,一种奢侈品取代了必需品。现在,它可能还会退回到第二个储藏室,这是17世纪和21世纪之间的一次不太可能的联姻。我们现在都是自耕农了。
新冠肺炎将给住宅室内设计带来的变化,大多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美国人已经开始后悔他们无处不在的开放楼层计划,这让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共享空间里。但在大流行之前,至少父母白天上班,孩子上学。现在,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家和家人在一起--多亏了视频会议,我们的老师、朋友和同事也都在家了。甘农说:“我们都撤退到了国内,但我们把每个人都拉了过来。”当我与他交谈时,甘农已经在他20世纪50年代2700平方英尺的牧场家中工作了两个月,笨拙地将开放的起居室变成了两个临时办公室。在任何地方,Zoom会议都是持续不断的,没有足够的安静、私密和合适的房间或空间来进行这些视频会议。郊区也不是无缘无故地被称为“卧室社区”的。
为了弥补专门房间的不足,有大量分隔空间的家庭可能最适合进行冠状病毒隔离。郊区大型住宅常见的简单设计,比如带有独立浴室的卧室,突然间模拟了公寓楼的私密性。对于那些有幸拥有它们的人来说,额外的卧室可以改装成办公室或工作空间。在疫情爆发期间,
美国人的住房很奢侈,从1973年的平均约1500平方英尺膨胀到2018年的2400多平方英尺。在大流行之后,记忆中对所有这些空间的新颖效用的记忆可以证明更多的这种做法是合理的。一些公司已经宣布他们打算让员工永远远程办公,房地产分析师预计会有更多的公司取消或减少昂贵的商业租赁,以节省资金。如果更多的工作场所提供这些好处中的一部分,那么家庭办公空间的吸引力(以及潜在的减税)等,可能会让郊区的大房子变得更加令人向往。男女步入式的壁橱已经很常见了,还有单独的主卫生间。随着开发的发展,他和她的办公室可能会出现在新的建筑中,或者作为现有住宅的翻新。
现有的郊区麦克豪宅也可能在大流行后找到新的生命。尽管批评家们认为这些房子在美学上丑陋、低效和奢侈,但许多家庭希望郊区的庞然大物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大家庭,比如父母或祖父母。随着冠状病毒威胁及其经济后果的持续,多代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各大学仍在研究学生是否以及如何在秋季及以后重返校园。而找不到工作或不愿搬到工作岗位上的应届毕业生,可能会在不确定的时间内回国。这座城郊城堡以实惠的价格提供了大量的空间,这要归功于它离城市的距离。
多代家庭代表着人口密度的适度增加,他们可以在此基础上使隔离变得更容易容忍。夏天就要到了,但是营地基本上关闭了,正常的家庭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春季的封锁也证明了在家中工作,同时方便孩子们远程学习是极具挑战性的。代际家庭提供了更多的人手和眼睛来照看孩子或管理用餐时间,这使得重叠的日程安排变得不相容。学校一直是住宅房地产销售的巨大推动力,即使是在线学习的小幅增长也可能震撼市场。经济压力可能会鼓励一些家庭整合到更大但人口更多的独栋住宅中,而将房价与学区脱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让他们更负担得起。
城市生活和郊区生活之间的其他妥协也是可能的。允许附属住宅单元(城市规划师对后院公寓的称呼)的趋势提供了一些隐私和户外空间,同时增加了密度,降低了住房成本。事实证明,中密度的多户公寓也很有弹性。邓纳姆-琼斯住在亚特兰大第一郊区英曼公园的一家翻新工厂里(现在就在市中心)。她的建筑很小,30多个单元散布在几座建筑中,所有这些建筑都直接通向户外。与郊区的生活相比,这样的安排更有效率,更适合步行。与全国各地爆发的木结构平台式公寓楼相比,这样的安排不那么密集,但更具抗传染性。随着城市生活变得更具吸引力,尤其是在千禧一代中,这些公寓楼已经在全国各地爆发。
这些公寓楼有时包含数百个独立单元,甚至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造成了管理困难。亚马逊、Insta、DoorDash和其他快递的增加已经使安全访问变得困难-更不用说包裹存储和收集了。冠状病毒使情况变得更糟,使送货和相关的人流量成倍增加,同时使电梯和走廊等公共区域变得更加危险。翻新这些建筑以适应社会距离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他们的便利设施,如社交厅和游泳池,突然之间也远没有几个月前那么有吸引力了。谁愿意为你不能使用或感觉不舒服的福利支付溢价?邓纳姆-琼斯解释说,当威胁最终解除时,千禧一代仍然想要过城市生活。但对冠状病毒时代的记忆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偏好。
杜尼,新城市主义的先驱,已经开始沿着这些路线重新想象居住空间。在本月的新城市主义大会上,他几乎是在讲话中提出了在冠状病毒之后建造联排别墅的初步想法。它取消了一楼的零售空间,将“象征性”阳台扩展为两层露台,并引入了专用的单位送货棚。这座联排别墅将洗衣房合并为靠近入口处的一间更大的精简房间,扩大了储藏室,并增加了一间“弹性房间”,这是对从以前普通世界进口的教室、家庭办公室和其他活动的新需求。
杜尼的设计完全是假设性的--这不仅仅是一项认真的提议,而是一种实践。但真正的房屋库存没有找到
而不是他们的刻板印象。这些小盒子可能都是一样的,但50年代的郊区地块也源源不断地涌入彼此,前院和后院畅通无阻,形成了统一的社区。而且这些社区在某些方面远不如他们的遗产召回那么同质化,即使红线及其严重的长期影响也是如此。
建筑历史学家芭芭拉·米勒·莱恩(Barbara Miller Lane)在她的“新世界的房子”(House For A New World)一书中记录了最早的郊区居民的多样性和强烈的社区意识。他们大多是低收入的工人阶级,大多数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与白领经理、秘书和个体户混杂在一起。这些社区是绝对隔离的,大部分是白人,但这意味着。
..